中国人的心灵为何越来越封闭?
中国人曾有如此大的气魄,但当代人的心灵为何却越来越走向危机和封闭?中国人的精神空间为何越来越逼仄、狭小和局促?
当代人的心灵为何却越来越走向危机和封闭?这依然关系到自然和良心问题。自然和良心本来是上帝的两面镜子,但中国人却越来越以镜子代替了上帝。
这就好比有位爸爸不得不离家远行数年。他的妻子天天给孩子看爸爸的照片。几年后,爸爸回来了。但孩子们拒绝承认这是他们的爸爸。他们把照片当成了爸爸。
这就导致了可怕的偶像崇拜。我们陶醉在大自然母亲的子宫中,或者陶醉在自己内心思悟深处,而忽略了去敬拜真的上帝。
我们以偶像取代了上帝。
上帝一旦不再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各种各样的偶像就纷纷登场了。
不错,我们的古人承认了神性,但却拒绝了神。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从正面来论述这一特点:
有位学者朋友给我写信,说我是“证明了神性,却不想证明神”。老实说,前半句话我绝不敢当,秉性愚顽的我只是用着傻劲儿,希望能够理解神性,体会神性;而对后半句话我又不想承认。不过确实,在我看来,证明神性比证明神更要紧。理由是:没有信仰固然可怕,但假冒的“神”更可怕,比如造人为神。
事实是,信仰缺失之地未必没有崇拜,神性不明之时,强人最易篡居神位。我们几时缺了“神”么?灶王、财神、送子娘娘……但那多是背离着神性的偶像,背离着信仰的迷狂。这类“神明”也有其性,即与精神拯救无关,而是对肉身福乐的期许,比如,对权、财的攀争。再比如,“乐善好施”也只图“来生有报”。
这不像信仰,更像是行贿或投资。所以,证明神务必先证明神性,神性昭然,其形态倒不妨入乡随俗。况且,其实,唯对神性的追问与寻觅,是实际可行的信仰之路。
首先,我不同意人可以“证明”神或神性。上帝的存在和神性其实都已“显明”在自然和人心。所以,我们找不到没有任何宗教的部落或民族。人心深处一定有某种不可磨灭的宗教禀赋。
改教家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之“认识上帝是人心的禀赋”一节中说:
“我们若要寻找毫不知道有上帝存在的人,恐怕只有在最愚蠢、最不开化的部落中才找得着。然而,正如著名的西色柔所说,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野蛮到不相信有一位上帝。即使在某方面与禽兽相去不远的人,总也保留着多少宗教意识;人心是充分地被这种与他们固有天性相交织着的普通原理所支配着的。
自有世界以来,既没有一家一国是完全没有宗教的,这就是默认,每个人心上多少总刻有对上帝的意识。偶像崇拜本身便足以证明这看法。因为我们知道,人是多么不愿意贬抑自己以高抬其他受造之物的。人以敬拜一块木头或石头,总觉比没有上帝好些,正足以证明人心对上帝有深刻的印象,要消减这种印象,比完全改变人的本性还要困难呢。人丢弃本性上的骄傲,自甘卑下到拜神的地步,这真是本性改变了。”
其次,我也不认同证明神性比证明神重要。正好相反,正因为神存在,这才显明神性确凿存在。模模糊糊的神性意识,往往不过是人性的自我投射。史铁生担心以偶像来代替神,却没想过虚假神性会代替真正神性。没有神的落实,何来神性落实?
第三,通过对比史铁生和加尔文的论述,我们就知道史铁生对偶像的看法有误。偶像不是因为本来没有神而试图证明有神才产生的,而是正因为有神却力图以假神代替真神而产生的。
偶像不是显明没有神,恰恰“显明”确实有神。这就像假币从来不会去仿造从来不存在的钱币一样。
在基督教看来,自然和良心是上帝显明自己存在的普遍启示。“启示”的希腊文原意是“揭开”,也就是上帝通过某些方式向人揭示他自己。第一种方式叫普遍启示,也就是上帝通过自然和良心来揭示他自己。本来这种方式没有任何问题。但后来,人类的罪影响了自然,更影响了良心。自然和良心本来都是美善的,但后来因着受到罪的玷污,就遭到了污染和扭曲。这两面镜子就脏了,也就无法清晰地照见上帝了。所以,上帝就采用了第二种方式来揭示他自己。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也就是上帝感动先知们写下他自己想说的话。这被称为特殊启示。
英国清教徒所写的《威斯敏斯特信条》(1646年),被华腓徳博士誉为“最齐全、最清楚、最周延、最完美又最生动的信条”。其开篇就说:
“自然之光与创造、护理之工,虽彰显上帝的良善、智慧和权能,叫人无可推诿;但都不足以将得救所必须的、有关上帝的知识和旨意给予人。所以,上帝愿意多次多方将自己和他的旨意启示并宣布给他的教会;此后,为更保守、传扬真理,为更坚立、安慰教会,为抵挡肉体败坏并撒旦、世界的恶意,就将此全部启示笔为《圣经》。”
这里提到的“自然之光”是自然之光和良心之光的合一。英文“自然”(nature)一词在中文中既可指“自然”,又可指“本性”。这两者的内涵在原文中都包括。而特殊启示,一般被称为“启示之光”,尽管自然之光也是上帝的普遍启示。但在林语堂看来,普遍启示之光是烛光,而特殊启示之光是阳光。他说:“太阳升起来了,将蜡烛吹灭吧!”
当然,太阳升起来了,有时候也还是用得到蜡烛。但有的人偏偏因着有了一点点烛光,就不愿意再走出去沐浴在阳光下了。
自然和良心好不好?好!它们都能帮助我们认识真理。但这两者并不是真理的故乡,它们自身也不能产生真理。当我们凭着自然和良心无法全面认识真理时,真理会亲自来光照、启示我们。这是真理的启示与慈悲。这样,我们才能认识真理。
在认识真理前,我们的理性、情感和意志首先需要被真理洁净和光照!这就像一个孩子的眼睛被涂上了泥巴,他在认出爸爸之前,需要爸爸先用清水帮他把泥巴洗掉。
庄子说到圣人之心像最干净明亮的镜子。这其实只是一种假设。禅宗大师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样的说法也是假设。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心没这么干净、明亮。
人生的意义必定在人生之外,绝对真理必定在世界之外。这意义和真理通过特殊启示的方式临到我们,我们才能产生真醒悟和真认识。不错,这个世界有其美丽,人心也有其良善,但它们都不过是那真、善、美的碎片和反映,而不是真、善、美本身。
每种文化所化之人都有其卓异之处,能看到某些真相;但也有其致命的盲点和错误。中国人看到了自然和良心的神圣及它们之间的神秘互动,认识到了普遍启示的伟大价值。然而,生而为人,我们已为万物之灵,跟大自然已截然有别;罪中沉沦,我们本心已污浊不堪。这两点正是中国人处理自然和良心问题时的根本失误之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结果,我们就越走越偏。再到后来,自然和良心竟成偶像,阻碍我们进一步向启示之光眺望。
这是多大遗憾!
中国人其实已发现自然中有一神秘世界,我们内心也有一神秘渴望。路易斯说人渴望“与宇宙中某个不可名状者再次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因为人知道自己应该与他紧密相联,否则,人就得不到满足。我们也“知道自己目前的状态是与他相隔的”,我们“也期盼着进入某扇门,一直以来我们都从外面打量着它,却不得其入”。要认识这种神秘联系,我们恰恰应该越过自然和良心,继续往前走,往上走,好走进启示之光,认出那光源的发出者——上帝。
我们的灵魂就像针,被上帝这强大磁铁吸引。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弗朗西斯·夸尔斯的贴切比喻。中国文化感应并检测到了自然和良心的磁性,却拒绝进一步靠近那磁铁。最终,那一点点的磁性也就慢慢开始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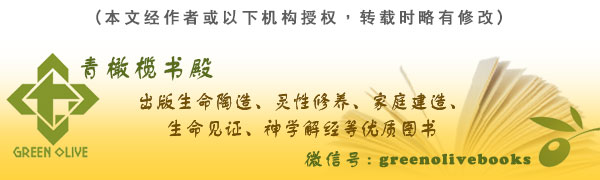
编辑流程:
发布时间:
繁體版:
Line?:
栏目:
机构: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