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类思想史上,尼采和祁克果曾经影响着千千万万个思考者或普通读者。尼采的那句名言“上帝死了”,以及他所宣扬的“超人”理论,成为许多人批判基督教的进路;而身为丹麦神学家的祁克果,虽然也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一生未婚,且性格忧郁,但并未走向理性主义的死胡同,而是终生仰望上帝。
在我读大学时期,祈克果曾是我灵魂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救星”之一。
我在刚进大学时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我的心灵之窗好像一下子被打开了。我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知识,除了《圣经》和神学之外,还涉猎了心理学、哲学、中国文化、美学、音乐等等。对我一个初出茅庐、信仰根基不深的理工科学生而言,这种囫囵吞枣式的涉猎,既不懂得循序渐进,又没有导师从旁协助,肯定会走火入魔的。
而在那个时期,存在主义的风潮正在校园中盛行。我也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心态下,开始读起存在主义的书,其中尼采的书对我冲击最大,几乎摧毁了我刚刚萌芽的基督教信仰。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我陷入信仰的低潮而无法自拔。尼采攻击基督教的言辞,既辛辣又鞭辟入里,令我无从反驳。这与那些拾人牙慧的好辩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最后,却是祈克果把我从漩涡里救出来的!
从某个角度来看,祈克果与尼采何其相似;但是从他们的思想和观点来看,他们又是如此南辕北辙!夸张一点来说:东离西有多远,祈克果和尼采相差就有多远!
以相似性来说,祈克果和尼采都是19世纪的人物,被并列为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两个人都才华横溢、著作极多;都终身未娶;都英年早逝(尼采死时才50岁);都出身于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尼采是牧师之子);都极力反对当代哲学宗师黑格尔的观点,希求突破理性主义的死胡同。
然而两人有更多的差异性。祈克果是忧郁而内向的,尼采是奔放而外向的(至少在他晚年精神分裂之前);祈克果是谦卑而自制的,尼采则是狂妄而近乎自恋的;祈克果反对国家教会的体制,但是内心却是极为虔诚的信徒,而尼采则是彻头彻尾的反基督教者。因此,两个人最大的歧异点,乃是在信仰的抉择上。
尼采坚信,人可以用意志不断地自我超越。因此他的哲学被称为是“超人哲学”,他强调以权力意志,来肯定生命的价值。他的崇拜者之一,就是希特勒。尼采最狂妄的名言是:
我的字典里没有“谦卑”这个字!谦卑是奴性,而我则是灵魂的贵族。我将“谦卑”留给任何一个甘心作奴隶的人!
他又曾激烈地批评耶稣说:“耶稣一生最大的错误,乃是他居然教导人谦卑!可惜耶稣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否则他会修改他的教义!”在19世纪的德国,敢如此评论耶稣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尼采的话极具煽动力,即使在一百年后,他的影响力仍然不衰。
但是尼采44岁时,却因为精神崩溃住进精神病院。7年之后,在世纪交替的1900年病逝。为什么这位意志超强,又强调以意志不断超越自我的尼采,却精神分裂了?这是哲学界迄今最大的谜团。最常见的说法是,他不是因为巨大的压力而精神崩溃,而是因为他20岁时,曾被朋友怂恿,与妓女发生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性关系,却因此染了梅毒。但是这梅毒病菌却潜伏了20多年,最终在他脑袋里发作,使他精神崩溃。那些热烈拥戴尼采的人,都接受此种难以置信的说法。
但是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Durant,《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却评论说,其实尼采的精神崩溃原因很简单,他是第一个亲自证实“超人哲学”行不通的人,所以他崩溃了!威尔·杜兰特还对尼采批评耶稣的话做了一个精彩的回应。他说:“可惜尼采批评耶稣时,他自己太年轻了——他才25岁;他又疯得太早,否则尼采会收回他对耶稣的这句批评!”良哉斯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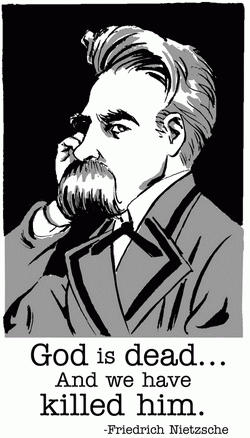
我在大学时期就曾被尼采哲学搞得神魂颠倒,却又苦思不得其解。直到我读到祈克果的日记,我才一下子豁然开朗了。祈克果对哲学家的评语(如前文提到的盖大厦的工人之喻),使我明白,在读哲学家的作品时,不但得“听其言”,还得“观其行”。如果哲学家的思想不能在他自己身上被验证,他的言论也就不值一顾了。于是我脱困了!这是我感激祈克果的原因之一。
祈克果对自己的一生和角色,无疑有一个明确的定见。在1847年的日记中,他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已经非常确切的是:我的作品已经对他人作了贡献,而且神赞许它,并在每一方面协助了我。我十分感谢他!因他对我无限的帮助,已远超过了我的希望。我的慰藉是在于,虽然我知道在神面前没有人能以任何功绩夸口,但他仍用赞许的眼光,注视着我的努力。并且由于他的帮助,我得以忍受我可怕的痛苦至它的极限。”
但同时,祈克果又不愿意被视为权威,因此他也在日记中写下:
以后我的每部作品,在封面上都应该这样标明:
诗的——以便显示我没宣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基督徒;
不具权威——以便显示我并没有将义务附加在他人身上,或去论断他们;
一种内心的苏醒——以便显示我与外在的变迁或此种类的改革无关。
2006年,我第一次访问丹麦,就很想去看看祈克果的墓地。对我而言,这有点像朝圣之旅。但是住在当地将近二十年的中国牧师,居然从来没听过祈克果其名!我到了之后,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找到他的墓。祈克果安葬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内一个平凡的公共墓园内,与父亲及家人同葬。这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墓,但是大概因为外国慕名而来的朝圣者太多了,墓园管理者还特别树立了一个牌子,指向这个祈克果家属的墓地。
在这里,我徘徊良久。抬头时,看到一群野雁掠空而过。我仿佛看到了其中一只扶摇而上的孤雁,直上云霄!
节选自:《迥别的祝福》,庄祖鲲 著;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