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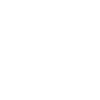
被怀念了两千年的诗人
一位诗人被一个用民族两千年的时间年年纪念,屈原对于中国人一定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即使是后工业社会的今天,端午节依然毫无争议地被中国百姓定为法定假日。
今天已经很少人知道屈原到底何许人也,更多想起的是吃粽子、赛龙舟,但是很多人会记得那几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我们知道屈原投汨罗江,知道他所写的《离骚》与《诗经》并举为经典,或许我们还有印象在我们的中学课本中,屈原被奉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但对于这位甚至被评为与莎士比亚、但丁、哥白尼并列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的祖先,普通的国人所知的可能就没有更多了。
然而,如果认真追溯端午节的传统,我们会发现,其实早在屈原出生之前多年,中国人就开始过端午节,起初只是为着健康卫生和民间崇拜的缘故。但后来人却执意将纪念屈原当做端午节的一个主要目的,可见古人对屈原之崇敬。
具体到中国从古至今之知识分子,屈原受爱戴之程度就更不必说了。喜爱推崇屈原之传统有文字可考者源自司马迁,经贾谊之《吊屈原赋》一路沿至毛泽东。司马迁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而毛泽东则评论道:“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列身屈原粉丝行列的还有李白、朱熹、鲁迅、郁达夫等等。
当我们进入《离骚》和楚辞的世界,即使今日读者有语言的隔膜,仍能感受到其想象之绮丽、情感之奔放、文辞之华美、构思之恢弘。如“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之流逝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之香草美人风;“驷玉虬以乘翳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余县圃”之求索之旅;“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之讥怨之辞。屈原的文学才华的确难以逾越,自诗三百以来的集体歌唱转而进入个人独创时代,出手不凡,浩荡长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亦鲜明地呈现出来。
如果我们能对屈原的人生轨迹略作考察,就能知道为何他有这样的感情又写这样的诗章。屈原开创一文学源流,是因为他走过的人生轨迹和精神指向与许多后来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暗合,他的遭遇极具代表性。
屈原的人生轨迹和精神指向
屈原的命运与楚怀王[1]紧密联系。起初,屈原官封左徒,为怀王所重用,也深得怀王信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然而,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中,怀王因为听信朝中佞臣如上官大夫、子兰等人之言,而屡出昏招,使楚国一步步走向灭国,而屈原也被人毁谤,不断被怀王疏远甚至流放。
楚王之昏庸今天依然让人觉得气愤。当时正值战国诸雄争霸时期,东北的齐国、西北的秦国和江南的楚国是三个实力最强的国家。在三国的较量中,秦国励精图治,很快显露出来。先是秦国欲攻齐,派张仪来楚馈赠于楚,且应许楚国只要楚不来帮助齐,战胜后,秦国会将自己六百里的属地割给楚国。在秦国强大的局势下,楚国本应联齐抗秦。可怀王因为贪恋六百里土地而与齐绝交。
而更可气的是当楚国派使者进入秦国接受赠地时,张仪使诈说:当初所应许的是六里地,何来六百里之说。怀王大怒,兴师攻秦,为秦所大败,斩首楚军八万余人,又进而取楚国汉中之地。怀王又举全国之兵前去攻秦。这时候魏国听闻,趁火打劫,袭击楚国郢都,楚兵惧怕而回,而齐国因为前嫌怒而不来救楚,楚国于是陷入大困局中。
战争相持不下之际,秦国决定将汉中地归还楚国以求和。可这时候,楚王被一己之气冲昏头脑,竟说:不愿要地,只要张仪的人头才能甘心。而张仪再入楚,又使钱又使诈鼓动怀王的幸臣宠妃在怀王面前巧言,怀王最终竟然连张仪也不杀而白白放走了。
后来秦昭王欲与楚国通婚,想要怀王前去相会。屈原劝告怀王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不能听信他们,不去为好。但怀王听其稚子子兰的话:不要做让秦国不喜欢的事。怀王最终去了秦国。而他到秦国后,秦国伏兵很快断其后兵,要逼怀王割地。怀王不听,逃到赵国,但赵国不愿收纳他,只好又返回秦国,不久后病死在那里。的确如司马迁的评论:客死他国,为天下笑。
起初怀王因上官大夫嫉妒、毁谤屈原而冷落屈原;顷襄王时,屈原又因谗言流放。有渔父看见屈原在江畔披散头发而行,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就问他说:这不是三闾大夫吗?何故而至此啊?屈原说: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因此而被流放。渔父说:为何不随波逐流,一定要怀瑾握瑜呢?屈原回答:不可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可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温蠖。
这就是屈原和许多中国文人的人生道路,他们的思想和追求其实也融入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血液中。
屈原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首先是学而优则仕。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或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中国读书人来说,诗词歌赋只是业余爱好,无论今天的人把他们的文学成就捧得再高,他们的政治理想若是在当时没能实现,他们的一生也都会是郁郁不得志的。无论是屈原,还是李白,还是苏东坡。即使有其他的安慰,不过是所谓的“聊以自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言壮语改变不了其人生悲凉的底色。屈原虽寻访古圣先贤,耕植花草田亩,因被君王放逐,国家衰亡,理想破灭,也终悲愤抑郁,投水而亡。
第二是寄希望于明君。因为专制政体,读书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得到君王的赏识和重用。即便后来科举取士,似乎有了更客观的标准,君王的贤明对他们的出人头地仍然极为重要。这就是屈原为什么常以美人自喻,称怀王为夫君;或称自己为香花,而那些佞臣为恶草。在国家危亡而个人理想亦不复有希望实现时,屈原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然而可惜怀王终不悟也。这就是易经中所提到的:“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命运交托于性情不定、悲喜难料的君王,也就注定了他们难以预料也必成悲剧的命运。尧舜只生活在遥远的古代,传为明君的三代君主也未必如想象之完美。最终只能悲叹“人莫我知兮”,忧怨而去。“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样的慨叹可能本身就是个错误。
第三是自视高洁。“把自己说得跟花一样”,这话用在屈原身上绝对没错。屈原用各种花草形容自己,表明自己内心纯洁、性情芬芳。这样的比喻,就是在今天看来都会让人有点儿难为情。但这绝对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共性,他们喜爱以自己的不同流合污为标榜,夸耀自己高洁的性情。无论是中学课本所选的《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云云,又比如王维的“墙角一枝梅,凌寒独自开”,还有刘禹锡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问题是:举世诚然皆浊,我真的独清吗?众人纵然都醉了,我却真的独自清醒吗?中国文人每每政治上不得志,便以品格高洁相标榜。这反映的首先恰恰是他们的失意,而不见得他们真的全然纯洁无瑕。
第四是怀才不遇而纵情山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屈原离开朝堂,游历于山川古迹,遍揽乎花树草木,纵情其间,欲以畅怀而不得。陶渊明在官场三十年而归田园隐居,说自己:“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多的人,如范仲淹之《岳阳楼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在政治上失意和苦闷中,在山水间稍得畅快,包括苏轼的《前赤壁赋》似乎在天地间找到融于造化之乐,但其实山水大自然并不能真正排解他们内心的幽暗。
屈原以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境和出路
本乎天上赐下的圣经真理,我们知道屈原以始的中国知识分子错了,因此他们的人生无法避免地走向绝境,他们错在以下三点:
第一,他们看错了自己。
屈原和中国文人虽然自己看为道德纯洁高尚,但他们真如自己想得那么好吗?所有的人想到自己的不幸的时候,都会觉得是因为社会太坏了,中国古代和现代的知识分子都未能例外。问题都是别人的,而自己是纯粹的受害者,但这并不是事实。人真的能在这个世界的罪恶上全然置身事外吗?从根本的意义上,有哪个人能说自己纯全无暇,迥异于世上所有人呢?
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主耶稣又解释十诫说:对弟兄动怒就如同杀人,看见女子动淫念就如同犯奸淫,难免地狱的火。(参太5:21-22)屈原不随从当时的奉承之辈,因而被放逐,这诚然显出他高洁的一面,但是屈原心中所信奉的道德理想,他真的全然行出来了吗?他真的如此毫无瑕疵吗?如同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不觉得自己不义,但保罗讲得清楚:“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罗2:13)法利赛人也是道德高尚的一群,但并不能因此称义,律法反倒显出他们的罪来,律法原是叫人知罪。
在欧洲,曾经有一家报纸致信许多作家,请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您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英国基督徒作家切斯特顿的答复只有一个字:“我”。很显然以屈原为代表的中国文人是不会这么回答的。他们会回答,是上官大夫,或者是楚怀王。中国文人需要摆脱自己根深蒂固并盲目的自恋和自义。他们需要知道上帝掌管一切,并按照他毫不含糊的标准审判世界,而且对于人一切的自视为好的、以自己的能力与道德抵挡神的行动,他视为不义。
罪的工价乃是死。(参罗6:23)某种程度上,百姓也在参与对道德英雄的塑造,是他们将对自我的期待投射到这些榜样身上,使我们和英雄自己一起用不符合事实的眼光看他们。反倒是这些英雄自己的自述能让我们看到群众的幻象。比如很有意思的,季羡林在他的自叙作品里袒露他年轻时的性挣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若能在真理光照下看到真相,觉察到主宰者之威严,也觉察到自己的罪性,那就是真正宝贵的转变了。
第二,他们怀抱错了梦想。
屈原和中国的读书人期待一个地上的国,期待在政治理想的实现中成就自己的人生价值。无论是因此享受荣华富贵,还是出人头地。一定要治国平天下,一定要在世上有所作为,才能表明在世上留下自己活过的证据。所谓立功、立德、立言,一定要留下点什么可以流传给后人,在地上永远流传。然而他们能留下什么呢?他们的身体最终会成为一堆黄土,留下给后人的丰功伟绩对后人可能有帮助,对他门自己又有什么帮助?而且后人也将死去,不复在世上。在这地上留下的名声和功业,对于他们有真正的价值吗?
圣经启示我们,这世界终将过去,有永恒的审判以及地狱之火和新天新地为我们存留,在世上积累的短暂的财富和名望,在天上毫无位置,而且指向的是永远的硫磺火湖之苦。况且即使在今生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东西容易变幻和倾颓。我们应当追求那永恒的国度、永恒之福分。
屈原及中国文人追求世上之国度,但他们并未意识到因为人性之败坏导致地上之国度并无真正之根基,而且转眼成空,无真正存留永恒之意义,而且伴随着变幻与毁坏。他们更未认识到,他们追求的国度,因为不以神为依归和倚靠,以政治理想为终极目标的人生其实是抵挡上帝。就好像犹太人和法利赛人一样,神要借耶稣带来一个永恒的天上国度,而他们追求的仍是让一个地上的王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独立和军事上的得胜,建立地上的荣耀国度。那其实是以人的国抵挡真正神的国。中国文人应该在对神的永恒计划的顺服中重新塑造自己的梦想。
第三,他们信错了对象。
屈原把他所有的期望放到了楚怀王身上,期待怀王能回心转意,期待怀王能重新信任并听取他的意见,期待怀王能做出明智和有利于楚国的决策。屈原把人生的一切期待和梦想放在他的君王身上。可惜这位君王屡屡犯错,而最终败国,且喜欢听佞臣的奉承之语,而不听忠信的谏言。于是屈原的人生只能不断滑落,以致最后殒身汨罗。屈原信了一个不该信的人。并非说他作为臣子不应该听从君王。而是说,他把他全部的人生押在一个鼻孔里不过有气息的人身上,这是没有智慧的。这也是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失败了是悲剧,成功了更是悲剧。
圣经中把这个叫拜偶像,也就是把不是神的当做神来拜,来倚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诗16:4a)拜偶像的,要和他的偶像一同灭亡。在受造和治理的秩序中,我们应当尊敬君王,但显然更为重要的是敬畏神。(参彼前2:17)那位真正掌管天地万有,且永远正直公平的耶和华,才是我们真正当信靠的。这位神满有慈爱,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对罪人的救赎,这位神并人的耶稣基督才是值得完全信靠的。我们认罪悔改,仰望他给我们的十架救恩,就能得着他所赐的永恒生命。在地上,唯独可信靠的就是他,在天上也没有别的可倚靠的。信靠他才是得着真正的智慧,而且可以有永不落空的盼望和期待。
因为这一位正是神所应许给人类的君王。在人类的整体堕落中,神从万族中拣选了亚伯拉罕,与他并他的后裔以色列人立约,要为人类兴起救恩。作为神的选民其实也作为人类的代表的以色列民中,曾兴起君王,如大卫者也曾深得神的喜悦,但即使是最好的君王仍然因为人性的败坏而有诸如淫乱和谋杀等邪恶的罪行。他曾与部下之妻淫乱,为掩盖罪行以诡计阴险地将部下杀害。神应许自己赐下一位君王,他的根源是在天上,他是神的儿子,但将由女人所生,来到罪人的世界,他要兴起作王,是公义的王、施行和平的君,带来永无穷尽的国度。在靠近屈原生活年代的两千年前,这位神的儿子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以血肉之体却度过完全无罪的一生,并以神迹和一生所经历的事应验了旧约一再应许的无数预言。他成为王并非在于他的尊荣和高傲,乃是他至尊贵荣耀却降卑舍命,流血死在十字架上,为要将他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他因顺服神而死在十字架上,神却使他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天,在天上为神作掌权的,直到永远!
这位成为我们真正美好的君王。正是他为我们带来了神永恒之国度,非人手所建立的。这永恒之国度绝对稳固,永不倾颓,藉着爱我们的基督的死和复活赐给我们。(参彼前1:4)屈原若信靠这位君王,就必不至于因国度的败亡而忧伤绝望,因着这国的君王是智慧与奇妙之耶稣基督。若人能信靠这位基督而进入这国度,今生也必在基督仁爱的统治和将来显现之国度荣耀的激励中,满有信心和指望跟随他而活,直到最后的新天新地!
屈原错了,他和那些古人已经没有机会改正这个错误。但今天我们却还有机会。“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可1: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原名熊槐(前360—前296),战国时楚国国君。如上文所引,这位楚怀王被诗人称为“灵修”。

来源:教会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