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落花开》是一部由马丹·普罗沃导演,尤兰达·莫罗、乌尔里奇·图克尔主演的法国传记剧情片。该片讲述了一战期间,一位清洁女仆成为法国画家萨贺芬的传奇故事。第34届法国恺撒奖上,法国文艺传记片《花落花开》横扫七项大奖,爆冷之余,也将一名在历史中鲜为人知的朴素派女画家的生平铺陈在世人眼前。
在世界的缝隙中,画出另一个长阔高深的世界
电影《花落花开》,在恺撒电影节上,囊获七项奖。我出门找碟,老板指着封套说,“就是这个,一个男人走在山坡上。”我说,“不是男人,是女画家。”
萨贺芬·路易很中性化,邋遢,臃肿,迟缓,一个法国乡下的钟点工,在不同雇主那里洗衣、做饭、酿酒,头发蓬松,好像面包。但女主角演得太好,透出一种智商不高的天真。没受什么教育,没出什么远门,没爱过男人,也没被男人爱过。开头二十分钟,有点想不通,电影要描写的女画家就是她吗?世界对她来说,只开了一条缝。那她又如何能够画出,一个比她经历过的世界更加长阔高深的世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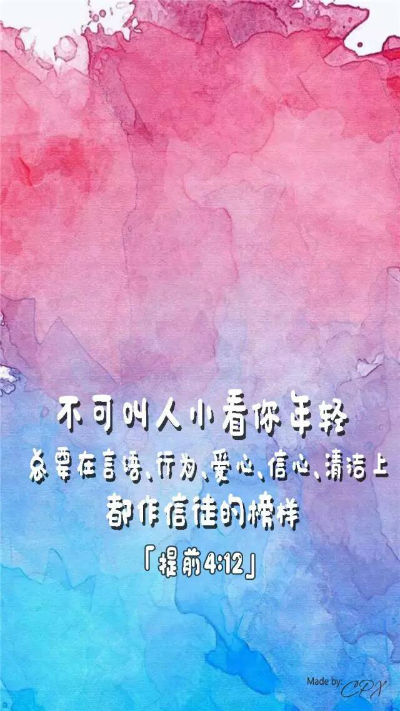
我到乡村,发现村民们对时空的记忆,都很含糊。若问远不远,他说很近,十分钟就到,结果我要走三小时。若问这东西多少年了?哦,怕有几百年了。若问九十年代的事,他说,很久很久以前。我的观察不够丰富,但许多村民对时空的感知,大致如此,就是空间都要朝近处拉,时间都要往远处推。想来也是因为“世界”对他们来说,过于逼仄。
“当下”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概念。绝望的意思,是没有意义的受苦,或没有意义的享受。有人的当下眼花缭乱,有人的当下死水微澜。人若活在劳苦愁烦中,这世界过去了五十年,还是过去了二千年,又有什么分别?我们活在一个很小、很确定的“当下”,却无法确知这一刻的意义。
其实这片子不关乎艺术,关乎终极的追问。一个洗衣妇,和这个宇宙有什么关系呢?她白天邋遢,生活委琐,被人唤来使去。世界对她而言,只有二十英里。世界到底有多大,关她何事?换言之,对她而言,宇宙被造得这么浩瀚,纯属浪费。但一到晚上,萨贺芬变了,她口里哼着赞美诗,手中拿着各种自制的颜料。她关起门来,世界一下子就打开了。她画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她能触摸的那些花朵、果实和树。她画不了更多东西,只能画一个不止二十英里的世界。

一次朋友和我讨论,据圣经的记载,或科学的假说,到底地球的历史、宇宙的起源,离我们有多远?我说,“容我说句粗俗的话,你要面对的真正问题是,地球有一万年,还是一百亿年,到底关你什么事?意思是说,你当如何接纳,如何拒绝;如何妥协,如何抗争;如何爱,如何被爱。如果你认为宇宙之长短,对这一切并无影响。我说,容我换句有文化的话,就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若不是德国的艺术评论家伍德,偶然住在桑利斯小镇,在另一家人餐桌边,看见了那家佣人的画,萨贺芬的世界,也许永远不会被二十英里外的世界知晓。伍德在一战前夕,面对现代文明的崩溃,挖掘了被他称为“现代原始艺术”的画家卢梭和毕加索。接着,他发现了洗衣妇萨贺芬。萨贺芬信仰很虔诚,在伍德看来略显无知。但伍德敏锐地看见了一种天才,就是这个傻乎乎的卑贱妇人,在她那近乎无知的脑袋里,有一种近乎得救的智慧。她的画中,住着一个广大的灵魂。看她的人,像一个褴褛的乞丐;看她的画,像一位荣美的公主。这使人不禁怯问:只是萨贺芬有独特的天赋呢,还是人人都是如此?我们不是乞丐,我们其实是王子?
萨贺芬看起来,没有一丝艺术气质。但看她的画时,你不可能轻视这个灵魂。萨贺芬的画,天真中有诡异,夸张中有拘谨,花朵像虫一样在动,果实像受伤的眼睛。茂繁的树,像亚当的族谱。
就如萨贺芬回答伍德,为什么开始作画。她说,1905年,守护天使在梦中告诉她,拿起画笔。从此,萨贺芬的夜晚比白天更长。她一作画,就脱离了她的“当下”。她的灵魂就从一个不到二十英里的世界,开始移民。她不再是一个钟点女佣,而是和伍德一样尊贵的人。尽管伍德的两次离去,深深伤害了她的尊严。她的生活,也从此和银河系、太阳系有了关系。就像世界大战以另一种方式使全世界都有了关系。不管地球历史到底多长,她的一生,这才和地球的历史有了关系。意思是说,和起初大地上的第一个人有了关系,也和将来大地上的最后一个人有了关系。

萨贺芬是否被这个世界知晓,对她和她的守护天使而言,并不重要。但透过伍德,她被世界知晓。透过这部电影,她被我知晓。在我看来,这就是天使催促她作画的原因。其实,萨贺芬若不是画家,她里面的世界,也一样尊贵而丰盛。但萨贺芬若不是画家,这个可怜的世界就看不到这种尊贵和丰盛;这个世界就不认账;这世界就继续藐视她,藐视所有和她一样的人。
对萨贺芬的精神失常,我无法完全解释。她的画展在巴黎筹备。不料大萧条朝夕来临,画展被无限推迟。伍德和这个世界一样,无暇也无力去承认和欣赏萨贺芬的尊贵。这使她倍受打击。一辈子独身的萨贺芬,为自己定制了华丽的婚纱,像新妇一样预备自己,献上自己的画。她对伍德说,画展不能取消,因为所有的天使都已出发,走在去画展的路上。
不只是这世界要看她的画,那个眼睛看不见的世界,也要来看她献上的画。萨贺芬说,她的画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拍照时,坚持将头仰起,闭目不语。但她终于疯了。她说,我的画受伤了,意思是她的灵魂受伤了。你们来看我的画,不是来看艺术,是来看灵魂的丰盛。
艺术可以被经济打断,灵魂怎么可以被经济打断呢?萨贺芬被送入精神病院,死在那里。
如果说,我们这三十年的关键词是经济,更早的三十年是政治,再早的三十年是文化。那么接下去三十年的关键词,就是信仰。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失魂落魄的时代。感谢这部电影,它让我更尊重家里的钟点工了,虽然小谢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画家,但她的灵魂,和萨贺芬一样尊贵。我也不怨恨守在楼下的居委会老太,因为我永远不知道,她的世界将在哪一刻被照亮,她的灵魂一旦苏醒,就要把这世上所有的财富都比下去。
我不知道,所以我祈祷。
原文标题:《天使们已经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