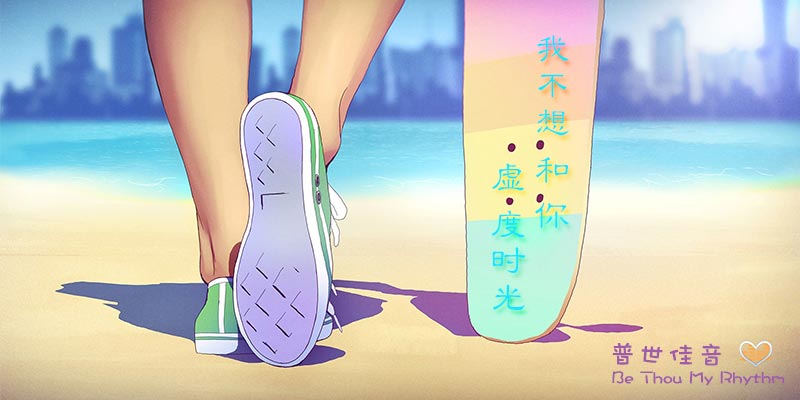当代基督徒对4-7世纪的基督教历史可谓极其陌生,而透过世俗文化所呈现的那几个世纪的大多数基督徒形象多半也是荒诞可笑的。很少有人客观地评价那段历史对于西方文明和社会的重要性,即透过切实地将基督教精神融入西方社会,才有了15世纪及其近代西方社会所确认的文明价值。
其中,隐修主义及其精神则又是最重要的路径,它使得基督信仰成为社会生活的真正要素。毫不夸张地说,隐修主义之于基督信仰在西方可以视为上帝在人间的真切的历史痕迹。无论今天对于隐修主义的某些极端的生活表达有多少不理解,无论隐修主义对于此世的离弃有多大的“荒谬性”和“复杂性”,毫无疑问,隐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远超过所谓的“时代”风尚,而绵延于西方文明精神的深处,已成为对世俗的抵抗。
迄今为止,隐修主义的各种精神要旨和规条仍在约束着西方世俗化的路径,约束着虽然日益为享乐主义所冲击似乎逐渐失控的现代性或者所谓的后现代性。
隐修之于世俗乃是一种“边界”。这种边界的生活形式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却是“中心”,是聆听上帝极重要的方式,甚至一度成为最重要的方式。当安东尼遁入荒漠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一无所有抱有最真切的盼望;当帕科里乌及其追随者奉献出全部的所有,组成社团,为穷人提供庇护的时候,他们必然信心满怀地生活在上帝的国度已经降临人间的信念之中;当凯撒利亚的巴西尔及其修道院强调社会事奉并且以慈善为隐修生活之记号的时候,基督教社群作为一种德性的垂范成为“慷慨”这种德性的最好诠释;当卡西安在恩典与自由意愿之间寻找平衡时,一种不为世俗掩盖的高贵成为世俗的出路;当本尼迪克把共同体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强调修道生活乃是一种严谨的必要性的时候,他在谈论天国的秩序。修道生活所寻求并尝试的灵性之旅,可能提供了失控的现代生活的解毒剂。
隐修主义兴起于东罗马帝国,迅速扩展到西罗马和整个西方世界。扩展速度极为迅速,几乎毫不犹豫地为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人们所接受,这就表明一定有一种令当时的人们怦然心动的意含,一定有面向上帝的节奏紧紧地吸引着当时的基督徒社会群落,一定有从隐修的基督徒生活方式中生发的急切盼望所构成的对社会沉沦烦恼的抵抗,也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准备好了接受这种生活方式。
基督徒们在隐修主义中发现了一种消解信仰之旅的张力的药引,因为正是这种张力成为世俗不断地袭向信仰的不安。在这个意义上,隐修主义正确地理解了信仰的真谛,即信仰必是对于世俗的约束,也必是对欲望毫不迟疑的审视。在新教精神兴起之前,这种在世俗中隐退的精神成为质疑世俗价值从而使得世俗始终以神圣的焦虑为前提的神圣之源。在世俗中隐修必须战胜世俗在自己身上的运用,既包括在身体上的治疗,也包括灵魂的治疗。在这个意义上,隐修主义给出了数个世纪人们生活的路标,它既不是一种哲学的闲暇,也不是不事劳作的寄生,而是劳作于上帝的祝福之中,使劳作成为对生活的各种欲求方式的抵抗。世俗的要素无论是其匮乏还是过分的欲求都被警惕,隐修乃是信仰投身于上帝的决绝的记号。虽然隐修生活对上帝的国度的理解可能并不是最好的,虽然生活在这样的国度仍然无法避免世俗的险境,然而它使世俗清晰地显示出诱惑人偏离上帝的种种边界。
当现代基督徒在一个过分世俗化的时代行走信仰之旅的时候,必须警惕他们也正行进在荒漠的危险之中,世俗作为荒漠的险境,常常渗透并成为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不易察觉的要素。因此在信仰为世俗包围并在世俗化的节奏中起舞的时候,世俗就随时会成为信仰的墓穴。就此而论,现代基督徒或许更应该去追随隐修主义者从荒漠的寂静中所寻找的安静己心地聆听上帝的路径。当我们今天以世俗的偏见批评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神圣生活的可能性时,更应该学习以隐修生活的“神圣偏见”,反思世俗化日益吞没我们所造成的心灵的“荒谬”。
原文标题:《隐修生活:现代信仰的解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