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守荆,何许人也?她哪来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向牧师之子传福音?她又如何带领一代宿儒,建立与上帝之间的父子关系?甚至让林语堂视她如亲,认她作干女儿,抚其晚年丧女之恸?

1930 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对中国所知极其有限,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译本《吾国与吾民》)1935 年一出版,彷佛瞬间揭去古老又神秘的面纱,中国不只让西人为之好奇惊艳,林语堂也一举成名,享誉欧美文坛。1937 年出版《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中译本《生活的艺术》》,更立刻被美国《每月读书会》评选为十二月特别推荐书,这也是林语堂所有作品中,译本最多、销路最广的著作。
然而,小小的陈守荆却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这么有名的作家,这么优秀的人才,净写些男人梳辫子、女人缠小脚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为什么不写上帝福音、拯救灵魂的文章呢?”初信耶稣不久的小女孩,就这么单纯的、火热的、持续的,每天为林语堂的心回转归向上帝、文字可以为上帝所用祷告,从未间断!陈守荆作梦也想不到,有一天,林语堂不只回到基督信仰之中,上帝还借着她的手、她的口、她的膝盖,让林语堂亲尝从未经历过的主恩滋味。
陈守荆和林语堂真正见面,是二十三年后的事──那年,林语堂七十一岁,陈守荆三十五岁。
1966 年,林语堂夫妇自美返台定居,机场入境大厅挤了满满的接机人潮。见到外甥张钦煌与甥媳陈守荆,林语堂格外高兴。对陈守荆而言,那个天天在祷告中记念的人,竟然站在自己眼前,而且还成了一家人!为林语堂的祷告,于是更加迫切了──因为当时的林语堂虽然已经回归基督信仰,却只是把基督教当“宗教”,没有切身的生命经历!
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林语堂准备着手编纂《当代汉英辞典》,需要一位秘书协助打字、写信、收集资料。“征秘书?只要他登一个小广告,多少博士、作家排队应征,甚至免费为他工作都愿意!可是他都不要!”那么,她又是怎么脱颖而出的呢?陈守荆笑着说:“这是上帝的预备,二十五位教会姊妹为我祷告的结果!”
原来,林语堂的草稿字迹十分潦草,他常说,全世界大概只有他太太看得懂他的草稿吧!透过林语堂太太外甥女、陈守荆表姐的主动推荐,林语堂拿了几份草稿让陈守荆试打看看,一开始她简直吓坏了,但一个转念,陈守荆马上请二十五位教会姊妹为她祷告:“上帝啊!求显明你的心意!知道我凡事都是为你而做,为的是将来可以荣耀你!如果这是你为我预备的,求你让林语堂看了我打出来的东西,心里中意。”说也奇妙,事就这样成了!
除了能力足以胜任之外,陈守荆的单纯与质朴也是林语堂格外疼爱这位甥媳的原因!当然,陈守荆的耿直,也曾经让林语堂一度为之气结。
“林语堂常说,他的信仰受我影响很大,其实我看到他还是有一点怕,毕竟他的学问那么大,我这么渺小。但圣经的话就是力量,我既然听了真理,就要告诉他。”话是没错,但陈守荆到底对林语堂说了什么呢?“我说,我们都是罪人,都要认罪悔改──你有认罪吗?”天哪!这么直接?那林语堂的反应呢?“他气死了!”说完,陈守荆也忍俊不禁笑了起来。
“如果我只告诉他:‘你很有名,全世界的人都崇拜你!’那他永远不会得救!所以我虽然怕,还是要讲,顶多不作他的秘书,卷铺盖回家嘛!”回想起当初的“憨胆”,陈守荆一点也不后悔。“刚开始他真的很生气,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跟他说话,就连他太太也没有。但是倚靠主,我就敢讲。后来他大概觉得我是晚辈,学问也没他好,就不跟我计较了吧!”
其实,不说话的林语堂心里比谁都清楚,因为那正是他从小听到大,甚至自己也曾经在主日学教过的圣经真理!而陈守荆日常的敬虔,他更看在眼里,那份生命中的沉静,遇事从不慌乱,总在祷告中得着平安的稳妥,可不是远离信仰的那些年任他如何钻研儒释道,却一直渴求而不得的答案吗?虽然已经回归基督信仰,却总是像少了什么似的林语堂,陷入长长的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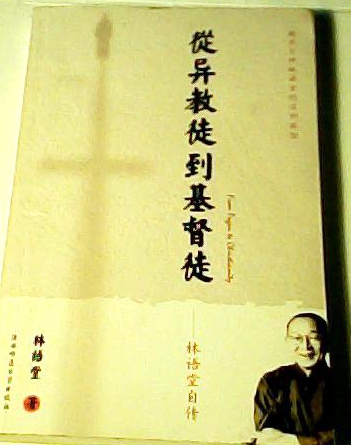
1971 年,林语堂七十六岁。大女儿林如斯因感情受挫、躁郁多年,最后竟自决身亡,让林语堂夫妇悲痛欲绝,耽忧至极的陈守荆对两老的关心照顾更无微不至。短暂前往香港女儿家小住时日返台后,有一天,林语堂约陈守荆到女儿的墓地追思,隔不多几日,林语堂主动开口:“守荆,我有三个女儿,现今失去一个,若你给我作干女儿,那就又复原了……”于是,继甥媳、秘书之后,二人再结父女情缘,这也带给林语堂晚年莫大的安慰。
然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大恸,却让林语堂的健康自此急速衰退;所幸,人的尽头正是上帝的起头──放手,或许是最困难、却也是最容易的答案,而困难或容易,往往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
有次,林语堂因为高血压住院,治疗多日,血压还是两百多,一直居高不下。正巧陈守荆到医院探望,自从青年时期离开基督信仰,即使老年重回上帝国度也从不祷告的林语堂,突然对她说:“打针、吃药都没用,你替我祷告,好吗?”说着说着,林语堂吩咐陈守荆把窗户打开,便和她一起在窗前跪下,虔心祷告起来。奇妙的是,第二天林语堂的血压果真降了下来!“你的祷告真有效!”林语堂笑着对陈守荆说。
回到基督信仰多年仍不赞成某些特定崇拜形式的林语堂,亲身经历这次上帝的医治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恢复祷告的习惯,也开始和太太、甥媳一起上教会做礼拜;以前老是不耐烦谢饭祷告、一心急着想用餐,现在则是每餐必要陈守荆谢饭祷告才开动;甚至每天晚上总要和太太、陈守荆三人手拉手,一起晚祷后才就寝。
身为第一代、且是家中第一个基督徒,陈守荆对信仰的坚持与火热,不只成就她和林语堂之间奇妙的见证,更为自己和家人带来祝福。除了陆续带领全家人信主之外,最有趣的是,为了传福音给最晚接受耶稣的三哥,陈守荆好长一段时间固定寄教会周报给三哥,谁知他根本不看,连信封都没拆就丢垃圾桶。坐在他座位后面的同事好奇捡拾,就这么周周“你丢我捡”,最后反倒是那位同事比他先全家信主!陈守荆的母亲信主之后也不遑多让,接连带领好几位朋友信耶稣,其中还有两位献身作传道人呢!
至于陈守荆与丈夫张钦煌全力投入服事的南京东路礼拜堂闽南语崇拜,更是林语堂晚年最喜欢聚会的地方,因为除了外甥、甥媳在此服事让他备感亲切之外,所唱圣诗、所读圣经无一不和他小时候聚会的情境相似,动情之处,总教他忍不住潸然泪下!
不过,最教人意外的,当属林语堂晚年回归信仰的见证,竟然成了蒋纬国信主的重要关键!这大概是陈守荆最始料未及的意外惊喜吧!
蒋纬国晚年健康欠佳,经常进出医院洗肾。他的肾脏科医师是个基督徒,很想传福音给他,却不知从何传起,便拜托就读国防医学院时期的团契辅导范大陵长老前去探望。
范大陵一见蒋纬国,马上立正:“报告将军,请问你认不认识范汉杰?”“认识啊!我的老长官!”“真巧!他是我爸!你看我和他长得像不像?”“一模一样!”范大陵一贯灵活,简单几句开场,马上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关系。随着话锋一转,范大陵突然冒出一句:“你和林语堂一样!”蒋纬国听得一头雾水,范大陵于是继续解释:“林语堂的爸爸是牧师,但那么多年他却没有信仰;你爸爸是基督徒,你也是这么多年没有得救。”
“林语堂回台湾,他的外甥媳妇向他传福音才真正信主。他自己说,他就像一艘船,纵横四海乘风破浪,直到晚年回到台湾才像船回到避风港,找到人生的目标。”范大陵说到这儿,蒋纬国随口提及自己在大陆也曾经受洗,只是一直没有真正信耶稣。那天晚上,范大陵就用林语堂的见证带领蒋纬国决志。后来蒋纬国过世,家属还特地打电话谢谢那位肾脏科医师。“家属不知道,其实是我带蒋纬国信主的,但那不重要,是谁带信主的又何妨?”范大陵一贯潇洒地说。
如同林语堂在《我的信仰》末了所说:“我的搜寻已告终结,我已回到家中。”家,不只是林语堂终于找到的心灵依归,更是每一个旅人渴求的避风港湾。而陈守荆,正是那个永不放弃,为每一颗漂泊的心导航的守护者。
原文标题:《林语堂的第四个女儿——陈守荆与林语堂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