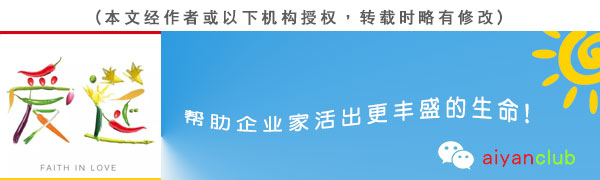对于90年代读大学文青来说,我们读着顾城和海子的诗歌长大。那时候天确实很蓝,日子过得很慢,写诗和现在互联网创业一样牛逼而自豪。后来我们也经历着成长、奋斗、结婚生子、人到中年,面对着人生下半场的尴尬和杂碎。
我们不再像90年代那样写诗,也不在草坪上弹吉他唱歌谈论梦想和诗歌,不会为了一个话题严肃认真地辩论。现实世界中,每天瞎乱“忙忙忙”,我们在咖啡馆里兴致勃勃地谈A轮B轮融资,在饭局上小心翼翼地顺应着话题,在手机上言不由衷地点赞。在朋友圈里我们功利地删掉对我们不重要的联系人,要么是毫无节制地“买买买”。门口是堆成山网购快递盒子,依然无法填满我们虚空的内心。
理想是飞翔的,现实则是个丑陋的面具,就如片中徐铮头上的那个大铁盔,戴上它,别人不认识你,你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我到底是谁?
电影港囧宣传说是关于中年危机,所以就去看了。电影信息量很大,段子很多,满目琳琅,但没有让人发笑和感动的地方,甚至你还没来得及感动,就已经开始恶心了。
电影刚开始,貌似真诚地探讨中年危机:一个怀念90年代初恋的男人,厌倦了当前的生活,想要偷偷和初恋见面,续写某种可能,在历经种种戏虐的磨难后,终于和当年初恋见面后。当你以为电影要带来一种可能性,或深入地探究中年危机时,然而,主人公自己却突然顿悟了。
莫名其妙地自己“和谐”自己,徐铮开始自己教育自己——我不该妄想,我不该出轨,我应该回归,我应该灭了各种冒险的尝试。最后徐铮选择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事业家庭两不误。影片结尾带给观众一种廉价的妥协和解。貌似三观很主流很正确,有点中年男人的“警世喻言”和心灵温汤的味道,但却让人感到恶心投机,没有说服力。
“初恋不过是中年男人卡在喉咙中的一根刺,我要亲自把这根刺给拔了”。最后小心翼翼地选择了安全地、有确幸地退回了安稳的轨道。
影片唯一让人信服的一幕是,当男主人公在酒店终于和旧日初恋相聚了,初恋离开片刻,男主发现酒店墙上无数男人的照片,全是初恋情人有交集男性的照片,主人公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初恋玩弄的男人们中之一,男主人顿时感觉吃了只苍蝇般恶心,然后就是顿悟,再后面就是悬崖勒马,才发现妻子才是“真爱”,“放下了”初恋,回头是岸。
与其说这是猥琐的中年男人真实而黑暗的心理写照,不如说是人性深处无限的贪欲在作祟。既想奋不顾身地去爱,自己不忠诚,又期望对方对自己是全然真心的。从这一点上看,电影里的徐铮和20年前的顾城,本质上是一样的。内心总想不断占有、占有占有。妻子和情人都要,真情和假戏都要。一旦发现不能得到,要么退缩要么毁灭。
只不过诗人顾城固执地践行了自己的欲望,在情感的王国里的成为“皇帝”,既拥有妻子还拥有情人的爱,自私又残暴,得不到就去毁灭。而电影港囧里徐铮,选择了看似明智地望而止步。机巧地妥协和回归,这种机巧无非是另一种功利罢了。
坊间多年前流传的中年男人四大快事“升官、发财、死老婆……”中国的中年男人难道都是这么盼的吗?20年前的顾城,三妻四妾的美梦,几千年来的男权至上似乎没变。
这是一部打着中年危机和情怀来赚钱的电影,提出了中年危机,却无意严肃地面对,中年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幌子。电影本是一锅大杂烩无法归类,制片方就给它贴上一个温情的标签,来吸引观众。一部商业片,无法苛责它什么,它如同片中的主人公一样,只能选择意淫和匆匆妥协。
中年危机的解药何在?
当年的情怀和理想主义是解药吗?
昔日的初恋情人和梦中偶像是解药吗?
当下的成功、舒适和安全感是解药吗?
于是,到处都是寻找的眼睛,眼神中又焦灼、愤怒、失望、悲伤、无神、呆滞。有人选择私奔,有人选择离婚,有人选择逃避,还有人选择无望地妥协。这世界是否真有一剂良药,能化解杂碎没有意义的中年危机吗?
当年的诗人顾城,至少给我们留下了“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诗句,留给我们无限思考。或许,顾城终其一生在寻找那光,很遗憾他没有找到。
关于眼睛,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其实,那光早就来到我们身边,而黑暗里很多人却本能地拒绝光。机巧地选择了躲在了舒适和安全的角落。一双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如何能适应光呢?
耶稣曾对跟随祂的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你选择痛苦地站立在那光下,哪怕是被穿透和炙烤?还是继续蜷缩在黑暗中,舒适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