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苦难,我读过杨腓力的《有话问苍天》。当我二刷此书时,几乎每页都含着泪读完,不能自已。
无他,只因“whereis God when it hurts”这个问题,正是我现在灵魂深处的呼喊。
9月份,刚刚确诊小女先天性耳聋的时候,尚不觉得十分痛苦,因为之前已经有种种迹象指向这个问题。在孕期已经被一次误诊的半椎体惊吓过,也预备过了。但之后,每次确认这个事实,都有一层加码的压力;同时又有体重增长停滞、大脑运动发育滞后等其他情形。我们不能不往更悲观的方向去假设:有没有脑瘫?有没有智力障碍?残存的听力会不会消失?在这些压力之下,连常规的夜晚哭闹也成了无尽的折磨。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夫妻几乎处于一种挣扎求活的状态,生存余力已经在负增长了。
这种情形下,到10月中,这个问题终于呼喊出来,拷问我的信心,拷问我与上帝的关系。
我所信的,是一位无力的神吗?或是一位冷酷的神吗?在这样的痛苦里面,这位神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想法?是要操练我的信心吗?那又为何让无辜的孩子承受这种折磨?
痛苦有什么意义呢?
杨腓力也苦恼于“痛苦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的确,身体疼痛是一个信号,让人意识到有危险或有病患;但车祸对于丧失肢体的受害人有什么意义,枪击事件对于丧亲的人有什么意义?
我女儿的耳聋,对于我有什么意义?——养育一个健康的孩子,尚且要耗尽心力。
基督徒喜欢从《圣经》中寻找痛苦的积极意义,若没有,那么神的公义或全能就要受到质疑——这是许多人这样做的动机。
——如果找不到,就无法回应不信者的责难。
——如果找不到,就无法为患难中的人带去安慰。
——如果找不到,神在自己心中的地位就难免动摇。
当然,当然,有些痛苦有其意义,就如保罗身上的刺,就如以色列的大腿窝。
在没有明确启示的时候,人类绝大多数的痛苦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痛苦本身只是由于我们身处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是由复杂的因果链与或然率强加给我们的而已。
承认这一点很难,承认后依然对上帝的全能全善和他的应许有信心则更难。
这个难题的转折点在于,将视角从追问苦难的原因转向探索苦难的结局。
从“为什么(why)”到“为什么(for what)”。
而在这种转折性思考之前,先要承认事实,以及承认因这样的事实而产生的各种情绪。
包括怨恨上帝、质问上帝。
如果没有一个上帝或者没有一个对所有事情负终极责任的上帝,那么怨恨谁,质问谁?概率论吗?
然而怨恨上帝、质问上帝的奇妙结果是:把痛苦中的人引向了认识(或更深认识)上帝,比如对患难者的安慰,比如对永恒的应许。
若没有这样的应许,我的女儿就要带着残缺的听力,遗憾地度过一生,与在她之前亿万的聋人,和她之后的亿万聋人一样,只是这个残破世界的一个无声见证;有这个应许,并且这样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以后也许也有她自己)就可以相信与盼望,终究有一天,她的耳朵会打开,一切美妙的声音可以自然地(而不是通过助听器或人工耳蜗的金属丝传导)触动她的神经,直达大脑中枢。那一天,她一切可能的身体或智力障碍,也都消失不见。她依然是她,只是完整的灵魂有了完整的身体。
除了这样的应许,同样真实并且带来意义的是,她的痛苦,并不在基督的十字架以外。耶稣当然没有耳聋,但他尝过痛苦的死亡,和死亡当中一切感官的消失。他并非不能体恤她的痛苦,以及我的痛苦。
在被卖的那夜,他曾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并不是说,他或我们要胜过苦难,而是胜过这个时刻用苦难捆绑人的世界。
痛苦本身没有意义,痛苦可能让人沉沦、沮丧、抑郁、丧失信心;痛苦中也蕴含着一种可能,就是更深认识上帝、在痛苦中得平安、甚至在痛苦中彰显上帝荣耀的可能。唯有这样的可能,才是有意义的。因着这样的可能,在痛苦中学会忍耐,变得成熟,是那种不至于冷漠麻木的成熟;因着这样的可能,在痛苦中磨去骄傲,磨去悖逆;因着这样的可能,把世界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He is here and is withyou all the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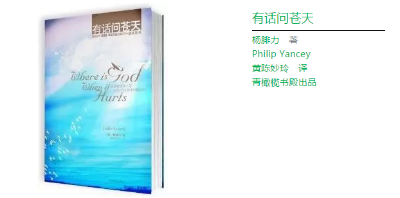
如需转载请注明:
文章来源:普世佳音,支持各大应用平台APP下载
新浪微博:普世佳音
授权微信号:耶稣基督圣经福音,wxbi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