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摘录:我们因与生俱来的骄傲,总以为自己是公正、无辜、圣洁和聪明的;除非我们因证据确凿而深知自己的不义、邪恶、愚蠢和卑污,我们若只注意自己而不注意主,就不能有这种判断,因为唯有上帝是这种判断的准绳。
我们惯于从人的角度看神,却不惯于从神的角度看人。以人观神,是把宗教放在人类学范畴进行研究,又把上帝放在宗教范畴加以研究。于是,无限的上帝就成了有限研究对象。宗教研究成了人类学研究的分支,属文化人类学范畴。宗教仅仅成了人类面对神秘未知时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和心理现象。
从大到小,我们依次看到:人、宗教、上帝。
以神观人,就是先以上帝存在为前提。上帝存在,故而才有形形色色对上帝的寻求,而这些寻求就形成了种种宗教。宗教是一切文化的基础。然后,我们再从宗教角度来看人之为人的本质。
从大到小,我们依次看到:上帝、宗教、人。
以人观神,是先假设上帝不存在。宗教就是去寻找一个并不存在的上帝。上帝不存在,但宗教偏偏去找并不存在的上帝,这就注定了宗教是人类心理的主观和错谬投射。人相信他愿意相信的。这是因信而灵。
以神观人,是先假设上帝存在。上帝通过外在大自然和内在良知来处处启示他自己。这被称为普遍启示。人对大自然作为普遍启示的回应,产生了文化;人对良知作为普遍启示的回应,产生了宗教。宗教不是人类心理的一种投射,而是上帝确实存在在人心深处的显明和印证。人以信心来回应未见之事和所望之事。上帝是灵,人的心灵回应上帝作为灵的存在,是为信。这是因灵而信。
中国文化惯于以人观神,属于典型的人本文化。一开始,中国文化有其强烈的灵性诉求,但可惜的是越来越淡漠。孔子认为君子“四不”和“三畏”:勿意(不臆测)、勿必(不主观)、勿固(不固执)和勿我(不自我),畏天命、畏大人和畏圣人之言。这都是谆谆告诫人不要坐井观天,不要自我中心,而要敬畏天命、尊重天道。道家向来提倡“以道观之”。
可见,中国文化一开始并不主张完全以人为本,而要求把人放在一个天道、天光笼罩的宇宙磁场中。韩愈说:“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但问题是,这高超天道、天命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先哲们总是语焉不详并“王顾左右而言他”。于是,中国文化越发展,天道和天命越来越变成人道、人心。与此同时,我们也大大忽略了人性幽暗和人心沉沦。于是,在实际运作中,天道和天命越来越往下,也越来越降低。
以道观之,也就越来越成了以心观之和以人观之。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写着:“认识你自己。”
但问题是:人到底怎么认识自己呢?
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从人自己来看人?还是从神来看人?
“自己”恰恰不是“认识自己”的出发点。
我如果要真认识自己,是从我自己开始,还是从我父母开始?当然,这得从我父母开始。我并不是使我开始的原因。对人类来说,恰恰不能从人类自身,而是要从人类的创造主开始这一自我认识之旅。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开篇就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得非常精彩、透彻:
真实的智慧主要是由两部分所组成,即对上帝的认识,以及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不过因为这两种认识相互的密切关系,所以二者孰先孰后,很难确定。
若是天使尚且因恐惧而蒙着自己的脸,何况污秽败坏的人呢?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主必做王。”(赛6:2,24:23)这即是说,当他更充分地表现自己的荣光之时,其他一切最光亮的东西,都将为之失色。认识上帝与认识自己虽如此密切地互相关连,但教导的正当次序必须先论对上帝的认识,然后论对自己的认识。
加尔文如此真知灼见地发现了认识上帝与认识自己的互动关系:不认识上帝,就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上帝;越认识上帝,就越认识自己;越认识自己,就越认识上帝。认识自己的正当出发点,则是要先认识上帝。“我们因为自己的不完全,而想念上帝的完全。”上帝的完全不只是一切完全之为完全的标准,也是一切不完全之为不完全的标准。
这是真正大智慧,其前提则是真谦卑,而不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狂傲。
《箴言》9章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这确是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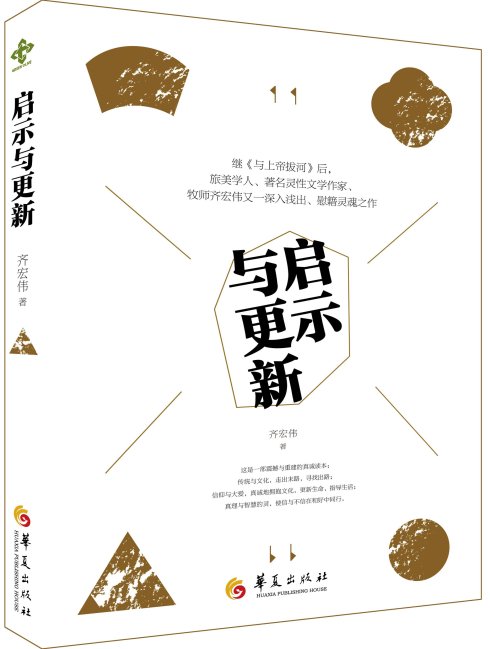
本文摘自齐宏伟老师的新书《启示与更新》,青橄榄书殿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