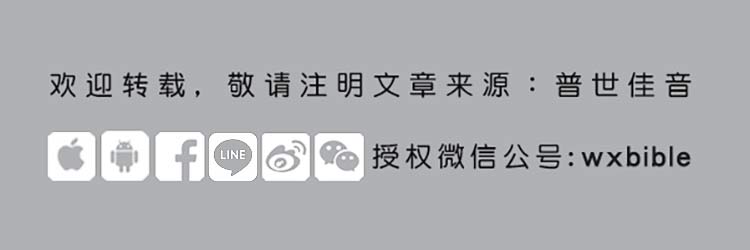舊約對當時社會和文化所採取的態度,能否教導今天的基督徒如何回應這個世代的社會與文化?
首先要說的是,既然舊約對不同的文化現象採取不同的回應,我們就不可能採取單純而簡化的立場。我們不該全盤接受社會中的文化,將之視為完全合適或值得包容的,但同時也不該全盤否定,視之為全然邪惡和可憎惡的。我們要有明辨和批判的態度。
全然摒棄
首先,舊約引領我們看見,人類墮落社會當中,必然有一些層面是上帝所拒絕與憎恨的,必須摒棄。對此,基督徒唯一能作的回應,就是棄絕和隔離。要如何辨認這些特徵,舊約也給了我們一些線索。大體來說,以下四種類型,特別為以色列的律法和先知傳統所譴責:偶像崇拜、歪曲反常、人身傷害和對窮苦者麻木不仁。這四項特徵與今日社會仍息息相關。全世界的人類文化有許多面向,明顯和這四個來自墮落人性的黑暗傾向有關。
在我們的時代與文化,難道不需要舊約那種嚴厲的態度,面對那公開且幽微巧妙的偶像崇拜?基督徒和以色列人一樣,容易不自覺地將上帝貶為只是救恩和主日的上帝,而在“真實生活”中膜拜物質主義的金牛犢和消費文化的巴力。敏於察覺到偶像崇拜是非常關鍵的工作,是先知性的職責,而且任何人若要在文化中揭露這樣的偶像,經常要付上極大的代價。
在這道德價值遭到質疑、面目全非的年代,難道不需要像舊約一樣,清楚揭露歪曲反常的行徑?保羅將偶像崇拜與扭曲真理緊密相連,有其重大的意義,因兩者的關聯不僅涉及性行為,同時也使整個知識環境,對真理有所歪曲(羅1:18~32)。
面對戕害弱者與殘害無辜之人,面對類似廟妓與獻嬰兒祭的習俗,難道不需要舊約那種義憤填膺的怒氣嗎?如今,色情的交易已取代過去在經濟上剝削女性和傷害孩童的模式(但後者其實根本尚未根除)。而舊約對這方面的敏銳度,會對殺害數百萬計尚未出世的嬰兒,發出什麼聲音?有些婦女是出於醫療的理由而墮胎,但絕大部分似乎只是為了圖個方便。
面對那些麻木不仁地“踐踏貧民的頭”的人(摩2:7;彌3:2~3的描述更令人膽寒),難道不需要舊約那種毫不妥協的批判?如果所多瑪的罪惡在於“心驕氣傲,糧食飽足,大享安逸”,對困苦和窮乏人麻木不仁、不扶助他們(結1 6:49),那麼絕大部分的基督教教會(尤其是西方教會),就是安逸舒適地住在所多瑪,而非錫安城。
相信讀者可以從各自的文化處境,列出被視為偶像崇拜、歪曲反常、人身傷害和麻木不仁的例子。這裡至少提供了一個架構,分析我們文化當中必然會有的負面因子。以色列蒙召摒棄、抗拒這些習俗。教會當然勢必也會有一番搏鬥。
有限度的容忍
其次,舊約中以色列的經驗,也幫助我們面對墮落社會的事實。連上帝都接受了這個事實!這就是為什麼耶穌說,起初上帝創造的心意是一生之久的婚姻,但是祂容許離婚是“因為你們的心硬”(太19:8)。如果離婚在以色列這上帝救贖的子民當中都被容許(雖仍有批評,同時也教導更高的標準),那麼在我看來,我們得同意,在世俗社會中離婚同樣是被允許的。這並不是說這個制度不該被批評,而我們也不只是要致力維護最高、絕對的標準,並使人靠近那樣的標準;這是因為在制訂法律時,必須寬容一些不那麼合乎倫理理想的情況。
在本書前一章提過,戈登·溫漢(Gordon Wenham)對於“律法所吩咐或禁止的事”和“社會認為其在倫理上可取或排斥的事”這兩者的差異,作了很好的討論:
在大部分社會裡,法律所強制執行的往往跟社會中的賢士認為應當去做的有段差距——更別提距離理想境界又有多遠了。道德的理想和法律之間確實存在某種關係,但法律傾向在立法者的理想與實際執行的狀態之間,作務實的妥協。法律只強制要求最低標準的行為……或用聖經的術語來說,公義絕不只是遵守十誡和五經中的法條……法律往往只為社會行為設立底限,而不是規定倫理的上限。因此,研究聖經中的法典,似乎就不是要揭示立法者的理想,而更可能是看出容忍的底線……(許多舊約律法中非法律性的勸誡)都指出,立法者的倫理理想,遠比他們所制訂的法律文字來得高 。
這原則必須應用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更寬廣的領域。很多時候,基督徒所生活、工作、應對的,都是顯然未能達到上帝標準的情況和體系。當我們像鹽和面酵一般致力於改變的當下,有些事是必須容忍的。
以一夫多妻制為例,這在西方可能已不是當前的倫理議題,但在世界其他角落的基督徒仍要面對這個題目,且需要倫理和教牧上的解答。若完全從聖經倫理的角度,我們當然必須堅持,在道德上,多妻制與上帝設計婚姻是一夫一妻的心意相比,的確有缺陷。耶穌針對離婚所作的言論,認為一個男人和妻子離婚另娶他人是通姦的行為,暗示了基督徒不應選擇再娶其他的妻子。因此,基督徒當然不應主動另外娶妻。但假若一個男人生活在多妻制的文化,已娶了好幾位妻子,然後成為一位基督徒,這又該怎麼辦?難道我們要說,他唯一的選擇,就是只留下一位,與其他所有的妻子離婚?若是這樣,舊約絕對會說——從妻子的角度來看——這是讓大惡來代替小惡。就像先前說的,舊約平衡的教導認為,較之於一夫多妻制,離婚是更加不可取的惡。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會為了容忍一夫多妻制,作一些務實的辯護。在他們的社會,女性沒有機會從事有獨立收入的工作,寡婦、離婚婦女、單身女性,也沒有社會福利的保障,沒有子嗣更被視為女性極大的恥辱。因此,以色列人會說,當然最好所有的女性都有一個歸宿;即使因此得踏進多妻的婚姻生活,也比成為娼妓或落入寡婦的慘境來得好。舊約所建議的方式似乎是,給予多妻制某個程度的包容,但同時也提出神學上徹底的批判,並且宣達更理想的標準。
保羅在談及婚姻和離婚時,也處理了類似的倫理問題。但若有人結婚時尚未歸主,但後來歸信基督,那麼他或她並不需要與未信的配偶離婚——除非對方提出要求,那麼保羅便同意那位信徒恢復自由身。他的原則似乎是,新歸主的信徒應尊重歸信之前所作的個人承諾。與未信的配偶維持婚姻,比新歸主的信徒提出離婚更為合宜。有人認為,保羅也會以類似的方式,容忍歸信的多配偶者(林前7:12~24)。
與此類似,雖然我們已立法廢除了奴隸制度(不過在世界各個角落還是有若干奴隸制度持續著,因此這只能是個語帶保留的陳述),但現存的經濟結構和工業生活,仍遠遠未達上帝對人類尊嚴的標準。基督徒必須某種程度容忍這些現象,才能在當中設法解決一些問題。觀諸舊約對正義、公平交易和憐憫至弱者等清楚的原則,基督徒當然同時也必須尋求改革和挑戰的機會。
我們甚至應該仔細思考,以色列容許奴隸制度,是否也因為這是比其他制度更為合適的選項。根據“奴隸”這個詞一般性的意義,有人立刻會說,要為奴役人類這件事辯護,完全不合理。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將另一個人視為財產一樣看待。但若看看以色列社會在處理負債者的問題時,採用抵押式的勞役服務方式,我們或許就會說,這至少有若干可取之處。債務人是同意一份協定,讓自己受債權人的約束,以勞力償清債務。這可能比現代社會所採取的方式更值得慎重考慮。現代社會對無法償還債務的處理方式,從宣告破產到入獄服刑都有可能。然而,前者只會使債權人什麼也拿不回來,似乎並不公道;後者則完全沒有好處,還要付上龐大的社會成本。正如本書前一章的內容所見,單就法律罰則來說,我們確實可以說,以色列以一段時間的奴役還債,似乎比我們采監禁的方式更合乎人性。奴隸仍舊住在家裡,在“正常”世界裡和人群一起工作。他行走在上帝的天空下,步行在上帝的土地上。相對地,監禁則拒絕給予這一切,而且有趣的是(不誇張地說),監禁從來都不是律法書所採用的罰則(但在列王時代後期曾執行過)。當然,如此比較的重點,不在於提倡恢復奴隸制度,或是想像在現代社會能有簡單的替代方案取代監禁,而是提出一個看法:當我們對奴隸制度有直覺的反彈卻輕易容許監禁的制度時,舊約會挑戰我們仔細思考這兩者的倫理(以及不那麼合乎倫理的)層面。我們會發現,我們能從舊約典範所學到的,超過我們的想像。
批判的肯定
第三,舊約也顯示,人類社會和文化生活中依然有值得肯定之處,雖然我們仍需保持明辨的心。教會歷史有太多這樣的例子,例如透過藝術、音樂、繪畫和戲劇來實現教會的目標,以淨化過的基督教內容取代原本的異教慶典。早在新約最早期的基督徒,為了讓聖經的福音扎根在希臘世界,為了用希臘文來表達福音及面對希臘哲學的挑戰,基督徒的宣教就一直積極而富有創意地投身在人類多元的文化當中。
既然全人類都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那麼,每一個文化就必然有一些部分能反映出上帝的本性,肯定創造的美好,體現上帝的道德標準,從而對人類的發展有所貢獻。當然,同樣在文化當中也有許多層面,掩蔽上帝的真理,詆毀受造界,顛倒上帝的標準,並致使人走向貧窮枯竭。然而,這不該使我們裹足不前,不去欣賞文化中值得肯定的美好。
節選自《基督教舊約倫理學》, 萊特/著,康培思文化策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