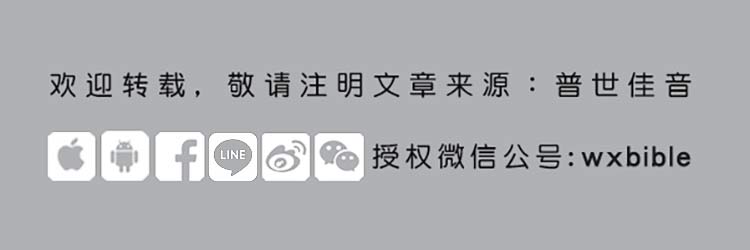這不是一個革命故事,而是救贖的故事。這不是一個希臘式的半神半人的拯救者。而是一位全神全人的犧牲。他承受的,是我們活該承受的。我們的活該,變成了他的活該。走向十字架的救主,表現的就像他真的活該一樣。
奧古斯丁說:十字架上發生了一次交換,就是以健全的形容,換來殘損的形容。道藏在一個卑微的形象裡。
以賽亞書53章以前,反覆說的都是一件事。就是人的罪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這是理解奴僕君王的前提。也就是認識恩典的前提。
人們常說,失敗是成功之母。但以賽亞書不厭其煩的告訴我們,失敗是失敗之母。失敗的結果就是繼續失敗。罪人不能生出義人來。
我們怎麼強調恩典呢,只有一個方法,就是通過強調罪。
所以,恩典的教義,不是使福音變得平易近人,變得聽起來合情合理。恰恰相反,越是強調恩典,越是得罪人。因為以賽亞書用了整整52章,來烘托這個恩典。只有你夠絕望,只有你厭惡自己,你才能認識什麼叫恩典。
然而,上帝預備了一件事,作為對墮落的人類的回答。
那就是一位絕對尊貴者,成為絕對的卑微者。絕對的無辜者,成為絕對的受害者。絕對的富有者,成為絕對的貧窮者。
革命者的受難故事,英勇就義者,總是氣宇軒昂。劊子手嚇得發抖。在這種革命美學中,將屈辱者塑造成鋼鐵戰士,光芒萬丈的形象。將加害者塑造成卑微的、畏畏縮縮的樣式。革命的受難故事,只是一種道德主義的故事。骨子裡還是一種暴力美學。
但耶穌,卻沉默不說話,為什麼不說一句話,背負著沉重十架。一步步走向各各他,甘心為我們被殺。卻低著頭,不辯護,默默的受苦。在53章中,這位沉默的羔羊,沒有半點英雄氣質。似乎這一切都是他活該承受的。是理所當然的。
這就是“贖罪祭”的意義。這不是一個革命故事,而是救贖的故事。這不是一個希臘式的半神半人的拯救者。而是一位全神全人的犧牲。
他承受的,是我們活該承受的。我們的活該,變成了他的活該。走向十字架的救主,表現的就像他真的活該一樣。他承受的,是我們理所當然的命運。但我們的理所當然,變成了他的理所當然。
因此,我們在這一幕中,看見的不是英勇就義的道德故事,不是就義之前發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講。我們看見的,是無法想像的順服。是不可能的順服。
那應該順服的,一輩子不服,還是不服。而那不該順服的,卻百般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屈梭多模說:基督成為肉身,活在卑微中。但這卑微只是從現世的角度去衡量。因為成為肉身的聖子,甚至在十字架上受盡羞辱時,也顯出驚人的恩典和美麗。
這是英勇就義的革命的受難故事所無法理解的。革命的藝術家們,無法想像,如果將一位受難的英雄,塑造成憔悴、枯槁,低頭,順服,默然不語的、逆來順受的樣子,那怎麼可能反映他的光輝形象呢。那不就搞砸了嗎。
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義和不義之間的交換,是生命和咒詛之間的交換。是榮耀與羞恥之間的交換。而這是以自我為中心、以人類為中心的唯物主義者和道德主義者所無法理解的。
福音包含兩點,一是絕對的有罪者,絕對的悖逆。二是絕對的無辜者,絕對的順服。
相信福音意味著,我的生命,是被那位絕對的無辜者的絕對的順服,所決定的。我的生命,建立在那位絕對的無辜者的絕對的順服之上。
信仰中,最核心的事,是那位絕對無辜者的絕對順服,成為了我的替代。我的命運,是由他決定的。我的命運,不是根據我做了什麼和沒有做什麼,也不是根據我怎什做決定的。而是根據耶穌已經做成的那件事,對,就是那件事,不是指他在海面上行走,不是指他使一個瞎子看見,不是他變水為酒,不是指他在世上做過的任何事,而是單單指向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復活。因為在十字架之前所發生的所有事,都是對這件事的預備。而在十字架之後發生的所有事,都是對這件事的解釋。
所以,只有一件事,是至關重要的。福音不是所有的事,福音就是這一件事。對你而言,也只有一件事是至關重要的,不是關於你的新工作,不是關於你在婚姻中的掙扎,關於你能不能買房子。不是關於你的任何重大的決定,甚至不是關於你目前的屬靈的狀態。對你的全部人生而言,只有這一件事是至關重要的,那就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與復活。
如果你不相信這一點,如果你沒有活在這件事中,如果這件事不是你的全部信仰的焦點和根基。那麼,你就活在一種“沒有基督的基督教”中。
來源:王怡的麥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