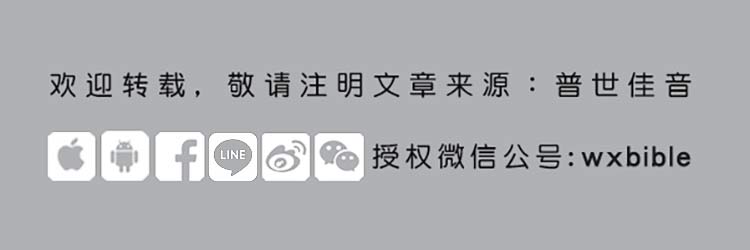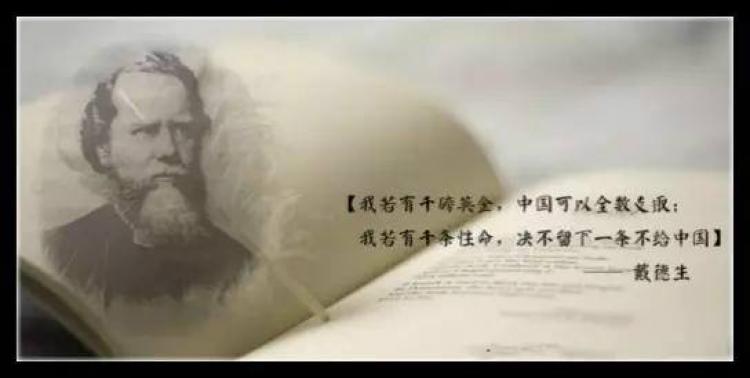他曾說,“假如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性命,絕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這位“中國內地會”的創始人,憑著信心,將福音從沿海推進中國內地,使基督的光亮照遍中國大地。他就是將一生獻給中國的英國傳教士戴德生。
事實上,若追溯戴德生的家族,便會發現,戴家的故事穿越兩個世紀,橫跨歐、美、亞三大洲,中、港、台三大地區,直貫祖孫九代人(戴德生為第四代,第五代為戴存仁,第六代戴永冕,第七代戴紹曾,第八代戴繼宗,第九代戴承約,他們依然為著福音奔走),而其中五代人與中國教會建立了血肉相連的關係。
那麼,是什麼樣的家族培育了戴德生這樣的巨人?
第一代:曾祖父 戴雅各(James Taylor 1749-1795)
戴德生曾祖戴雅各原居英格蘭南約克群洛士頓。1776年初的一次露天布道會,改變了戴雅各的一生,也改變了整個戴氏家族的命運。沒人知道,那一天,戴雅各是否扔過任何雞蛋,但是神的話顯然擊中了他的內心。那天的經文是約書亞記24章15節:“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幾天後的2月1日,是戴雅各的大喜之日,那天,他走在麥地裡,一心想著新娘和婚禮,但是這句經文竟再次無聲地擊中他,聖靈的工作是那麼強烈,以至於他不得不屈膝降服,請求耶穌基督成為他個人的救主。這一場屬靈爭戰下來,等他換完禮服趕到教堂,新娘與眾親友正望眼欲穿等著他。這一日戴雅各成了新造的人。從此戴家成了與神立約的家族。
十八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正展開,社會正義淪喪,英國國教僵化。布道家約翰·衛斯理,強調重生得救、追求完全聖潔,並注重社會關懷與社會正義,為英國帶來屬靈大復興。自1738年他經歷聖靈更新,至1791年去世,53年間他騎在馬背上行過238,500哩路,講過42,400篇道,但他並非一帆風順,也曾經歷很多的坎坷。譬如在英國北部約克郡(Yorkshire)的邦士立鎮(Barnsley)的居民,有很多人激烈反對他。
年輕的戴雅各原來也曾擲雞蛋扔石頭,加入反約翰·衛斯理的行列中。但自結婚之日經歷聖靈重生後,便帶領妻子同心事主愛人;雖屢遭逼迫,甚至只眼遭反對者揉入玻璃碎片,幾乎眼瞎,仍不改心中喜樂;並在家中聚會,成為邦士立第一位循道會地方傳道。1786年約翰·衛斯理以83歲高齡來到邦士立布道,夜宿戴雅各家中;賓主促膝論道,次日盡歡而別。五年後出身泥水工的戴雅各與當地循道會信徒同心興建禮拜堂於針迭山上,1794年完工。十多年後教會日益興旺。
第二代:祖父 戴約翰(John Taylor 1778-1834)
婚後兩年,戴雅各夫婦生下一個兒子,取名戴約翰,從事紡織業。戴約翰17歲那年,戴雅各去世。年輕的戴約翰繼承父志,也成為當地有名的帶職傳道人。他與妻子主辦的主日學,左近村鎮報名的孩子竟有六百名之多。孩子們入學不久,品行操守顯著提高,使很多反對者開始參加教會,當年戴雅各所建的小禮拜堂已不敷使用,會眾自發奉獻,興工建造了一座新教堂。
第三代:父親 戴雅各(James Taylor 1807-1881)
戴雅各出生於馬禮遜(1782-1834)啟程赴中國宣教之年——1807年。與中國人避諱長輩名號的習俗相反,英國家庭紀念長輩最常見的方式,就是給孩子起同樣的名字。為了紀念自己的父親,戴約翰使自己的兒子與其祖父同名。
戴雅各19歲便擔任循道會地方傳道,24歲學成返鄉開設藥房,藥房設於齊賽街21號,正對著最熱鬧的市集地。同年與賀雅美結婚;婚後讀了一些關於中國的書,特別是賀爾艦長的<遊記>,不由得對中國產生了負擔。一次,當他讀到出埃及記13章2節“凡頭生的,要分別為聖歸我”,便與妻子一起跪下來回應神的話,許願若神賜下的是兒子便將頭生子歸給耶和華。
冬去春來,戴雅各一家終於迎來了他們的頭生子,這個孩子便是戴德生。戴雅各對戴德生的品格養成影響非常大。戴德生四、五歲時常隨父親約克群鄉下傳道,對不認識耶穌的人特別同情,常立志長大後要到中國宣教。七歲那年(1839)循道會慶祝大復興百週年紀念,父親常帶領全家人一起讀巴彼得的書<中國與中國人>,其文字與插畫甚得孩子喜愛,他們一讀再讀以至四歲的戴賀美也夢想要跟哥哥一起到中國去傳道。戴德生的母親賀雅美也是一位敬虔的信徒。她為戴德生兄妹奠下美好的屬靈根基。
第四代: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
雖然在敬虔家庭長大,進入銀行工作的少年戴德生開始偏離信仰,這使他的母親和妹妹非常憂慮。
1849年6月,戴的大妹在日記中寫到,“每天為哥哥悔改祈禱三次”;一日戴母到巴頓的姨媽家作客。午後她為德生得救的事心中十分逼切,決意除非蒙神應允絕不停止禱告,也不踏足房外。數個鐘頭後她得了平安,開始讚美神。而那天休假在家的戴德生走進書房,無意中撿起一張福音單張。他一心只想知道前半部分的故事,若是看到任何陳腔濫調的說教就丟掉。然而,因著家人的代禱,聖靈吸引了戴德生的眼睛,當他看到,故事中的主人翁聽到耶穌在十字架上大喊“成了”,便悔改得救,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原來自己的罪債,和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樣,都早已由耶穌基督所付的代價做出了完全的補償,自己只需憑信心接受主所成就的救恩便能得救。於是,他跪在書房內認罪悔改,接受耶穌成為他個人的救主。戴德生欣喜地與妹妹分享這件事,又囑咐她不許告訴別人,包括父母。而在五十英里外的戴母,經過數小時與神摔跤式的禱告,也已確信自己的代禱已蒙應允。幾天後回到家,她直接問戴德生,發生了什麼事?戴德生以為妹妹告訴了母親。戴母卻說:“不,那天我為你禱告的時候,便知道神已經垂聽並悅納我的祈求。”那年,戴德生十七歲。
得救後的德生內心被極大的喜樂充滿,迫切地要將一切奉獻給神,多年後他回憶說:“清楚記得何等喜樂,我將愛傾倒在神前,一再向祂表明我對祂的感激之情,當我無望之時祂已為我作成一切。我求祂讓我為祂作一些事以表明我的愛與感激;一些捨己的事無論多麼艱難、多麼渺小的事,只要能得祂的歡心。我清楚記得當我將自己毫無保留奉獻在祭壇上時一種神聖莊嚴的感覺深深地臨到我,我確知祂已悅納了我的奉獻。神的同在成了不可言喻的真實與祝福。我深深記得當我俯伏跪在祂面前時那不能言說的敬畏與喜樂充滿我。雖不知祂要我作什麼,卻深深知道我已不再屬於自己,這感覺直到如今不能磨滅。”
戴德生獻身立志到中國事奉
1849年6月重生得救的經歷成了戴德生一生的轉折點。12月一個晚上他寫信給大妹說他極其渴慕過聖潔生活。那晚他在神面前表明只要神保守他不再跌倒,任領何往、任遭何事,他都願意為主擺上。日後回憶說:“我永不忘記在全能神面前與祂立約,幾乎要退縮,但已不能,……從那時起我深信已蒙召到中國,直到如今這信念不曾離開我。”從那時起他開始為中國而活。他母親說:“從那時開始他的決心已定。他的追求學習無一不以此為目標,不論遭遇任何困難,志向總不動搖。”從獻身之日起戴德生將一切舒適用品送人以過簡樸生活;加強運動以鍛練身體;外出布道慰問病人以操練愛心。他借到宣教士麥都思(1796-1857)於1838年在倫敦出版的《中國:現況與展望》,得知醫療在中國宣教的重要性,決定學醫。他同時聯絡在倫敦的“中國協會”,那是與郭實獵在中國宣教有關的福音機構,向他們表明到中國傳道心志並在代轉奉獻的小事上學習忠心;日後他常說:“小事是小事,在小事上忠心,卻是大事。”
1853年6月“中國傳道會”總幹事柏德緊急找到戴德生,力勸他接受差派。戴德生接受了,但與未婚妻韋瑪莉的婚約卻因此解除,因為瑪莉的父親反對把女兒嫁到中國。1853年9月19日戴德生登上“敦費士號”前往中國。此後156天“敦費士號”成為戴德生暫時的家。
1854年,戴德生到達中國後,先在上海、汕頭等地傳教。1857年定居寧波,成立了獨立的“寧波差會”。1860年,戴德生回到英國,開始招募傳教士,兩年後,他將在英國布萊頓招募到的寧波差會第一位志願者宓道生(James Meadows,1835-1914),派遣回到寧波。1865年,戴德生將寧波差會改名為“中國內地會”,簡稱“內地會”。
從1865年內地會建立扎根時期(1865-1875)36名宣教士,56個福音站,28座教堂開始,經過拓荒啟(1875-1885),國際化時期(1885-1895)至世紀交替時期(1895-1905)宣教士發展到825名,福音站721個,會堂703處,教堂418座,學校150所,中國同工1,152個,受洗人數18,625人。而戴德生後人,戴存仁、戴永冕、戴紹曾、戴繼宗陸續到中國宣教。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樣,而父母在信仰上帶給孩子的影響更是非常重要,戴德生家族就讓我們看見父母在信仰上對孩子的影響以及上帝的信實和奇妙。今天,當我們在關心孩子的身體、學業、未來的時候,願我們更看重孩子的信仰。父母的榜樣和禱告,真的可以改變孩子的一生。
摘自:亦文《“九代奇恩”與今天的中國教會》,《中國內地會簡史——記念中國內地會成立140週年專輯》,有刪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