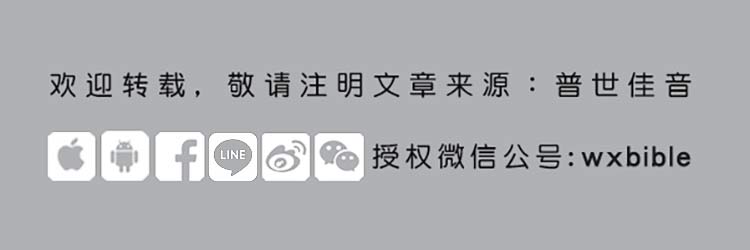《韋氏大辭典》對宗派的定義為:宗派乃是一宗教組織,其中各個會眾因著共同持守某些信條與禮儀,而彼此聯合。
瑞契(Russell E. Richey)是埃默裡(Emory)大學的資深教授,研究教會歷史四十年之久。從他聯合衛理公會的背景,他以為,宗派是自願的,因此它需要以合法性、實質上的寬容和宗教自由為預設條件,也只有在此環境中宗派是可能的。毋庸置疑,瑞契是以西方民主自由的社會為前提,來分析的宗派的產生。
事實上,任何信徒都可自發地加入或不加入宗派。如此看來,宗派必然是存在於宗教多元主義或是宗派多元主義的情形中。[1]
宗派必然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宗派本身無疑是合理的、自給自足且美好的“教會”。既然它是自動組成的,所以,宗派會承認其他教會的真實性,然而對於其他的教會群體,並不是一視同仁地接納,因為有時它並不承認一些宗派是正統的。
然而,在一些宗教自由受限制的地區,宗派依舊可能發生,但需要更多的“處境化”。今天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的發展,逐漸具備宗派的特色,以相同的教義和禮儀來彼此聯絡,形成了友誼和互助的關係,來拓展神的國度。按著韋氏辭典的定義,中國不少家庭教會的團體其實已經是“宗派”了。
當初路德所以脫離天主教,創立路德宗,是因為他認為,當時天主教的教義和作法已經違反了聖經;所以他主張“唯獨聖經”。然而“唯獨聖經”的提倡,卻導致後來無數新宗派的產生。有學者統計,現今至少已有三萬八千到四萬個宗派。
然而,教會的分裂都是“唯獨聖經”惹的禍嗎?究竟“唯獨聖經”是什麼意思?馬丁·路德主張的“唯獨聖經”,基本的精神和意義為何?最重要的是,“唯獨聖經”真的合乎聖經嗎?
在《基督教危險的觀念》一書中,麥葛福(Alister McGrath)指出:“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核心概念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明白聖經,且有權利來解釋聖經;此外,他們堅持別人必須認真地對待他們的觀點。結果,安立甘主義和其他的抗議宗教會應運而生。然而,這種對屬靈民主強而有力的肯定,卻造成了對教會穩定的威脅。最後釀造分裂,且形成了許多分離的團體。”[3]
教會歷史學家諾爾(Mark Noll)在接受《今日基督教》雜誌採訪時指出,在釋經上、個人生活中、公共領域的見證、及在威權統治的環境中,“唯獨聖經”的運用都會帶來混亂與分歧的看法。而後兩者的複雜性更是十分不容易解決。[4]
因此,不少學者把今天基督教會內部五花八門、彼此批判、派別林立的混亂現象,歸咎於“唯獨聖經”的提倡。
有鑒於此,范浩沙(Kevin Vanhoozer)在2016年出版了《巴別塔後的聖經權威》,意圖澄清“唯獨聖經”的真義,免得有人繼續把教會中解經的亂象所帶來基督身體的分裂,完全怪罪於宗教改革。
究竟改教家們所倡導的“唯獨聖經”是何含義?
第一 ,“唯獨聖經”絕對不是“只有聖經”(Solo Scriptura)。首先,改教家們以為,聖經的明晰性和充足性必須予以肯定,然後用“以經解經”的原則來處理聖經的解釋。當然,它持守“部分解釋全體,全體解釋部分”的原則,並且指出“較不清楚的部分必須按較清楚的部分來理解”。換言之,以經解經是強調,聖靈在聖經裡,在神教會的情境中講論基督。最終的解釋權威來自神,不是某個外在的訓示,或是內在的啟示。[5]
第二,“唯獨聖經”不是允許宗派主義的偏方,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它乃是一個呼召,要人聽從聖靈,就是祂在歷史裡於教會中對聖經所作的解釋。改教者並非不重視傳統的權威,只是當教皇和教會議會的結論與聖經清楚的教訓牴觸時,他們只能順服聖經。
第三,“唯獨聖經”所產生的聖經論,不是天真聖經論(“只有聖經”),而是批判聖經論(肯定聖經具至高權威、能決定其含義、連結真理,同時也承認人的解釋只具次要的權威、有多元性、可能犯錯) 。“批判聖經論”必然帶來釋經的多元性,因此針對一些容易產生爭論的經文時,解經家為不同意見總是留有餘地。
第四,純新教的“唯獨聖經”操練,即是按大公性聖經論進行(接受初代基督徒的神學判斷,也向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團體請教)。[6] 改教的精神應該是樂意向各地的釋經團體請教,因此不宜把自己的觀點絕對化。
由此觀之,倡導“唯獨聖經”的確會產生新的宗派,但它卻不應被視為教會分裂的根源。贊成批判式聖經論的立場,的確會在一些次要的問題上產生分歧,因此在歷史的進展中不斷有新的宗派發生。
宗派和宗派主義不同。如何理解“宗派主義”呢?簡單說來,宗派主義者乃是主張:加入宗派比不加入宗派更好。有些宗派主義者認為,自己所擁護的宗派是最忠於聖經的,把該宗派所持守的教義與“真理”劃上等號。持這樣信念的人會不斷批判其他宗派,認為他們都偏離聖經。宗派主義者把相對性的教義視為絕對性的真理,讓基督的身體四分五裂,無法合一。
范浩沙在《巴別塔後的聖經權威》一書中,於“唯獨神得榮耀”這章中探討了宗派主義。范氏以為,宗派主義的真實內涵並不容易界定。根據他的研究,他把宗派主義分為三類:弱式宗派主義(weak denominationalism)、激進宗派主義(radical denominationalism)、強式宗派主義(strong denominationalism)。[7]
弱式宗派主義是指,在宗派裡的信徒無法提供強而有力的理由,來為自己的存在或本質作辯護。而當這些信徒對於神學的委身不夠看重時,就會帶來很棘手的問題。這也會讓一些有可能加入他們宗派的信徒,找不到特別要加入的理由。
與弱式宗派主義形成強烈對比的,就是激進宗派主義。這些宗派的信徒熱烈推崇自己所認可的穩定結構、身份和傳統。這種宗派有時會發展為“教區式”的組織,且把自己的宗派偶像化。這就會產生嚴重的問題:把對宗派的委身當作是對基督的委身。
很明顯,這類激進宗派主義第一個試探就是“驕傲”,以為自己的宗派才是唯一的真教會。尤有進者,這類宗派傾向於發動對其他宗派的“戰爭”,企圖讓其他宗派消失。第二個試探就是,激進的宗派容易熱心擴展自己的宗派,取代了對福音的熱心。
而“強式”宗派,是提供“一個架構,讓虔誠的信徒在彼此看法不同的實際事務上,可以循法處理。”
范浩沙說:我們追蹤一個宗派的起源,往往可以發現,它是出於一個特別的神學或宣教危機(如,路德宗)。從這個亮光來看,宗派的形成是基督徒福音使命歷史的一部分,原本是為了將福音處境化,以配合一個特殊的情境,結果卻產生了超越處境的持久影響。屬於強式宗派的教會對自己的膚色很有自信,因而願意與其他宗派合作。他們的自我形像很健康,其中包括明白自己的偏見所在:“沒有一個宗派能完全包攬當下宇宙性的教會。”[8]
筆者以為,范浩沙的觀察與反思相當正確。健康的強式宗派通常有豐富的資源可以幫助地方教會,使她在遇到困難時,有較妥善的解決機制。倘若沒有宗派的扶持與資源,單獨教會在發展過程中常有無法突破的瓶頸。
在1949年之前,神州大陸的教會絕大部分是由西方大宗派的差會建立的。十九世紀是英美大量派遣宣教士進入亞洲的黃金年代,海外宣教的浪潮在歐洲及北美洲各地席捲。根據維基百科提供的資料,到1925年時,在中國的西方宣教士,連同孩子在內,數目已達八千人之多。這些宣教士來自公理會、聖公會、信義會、浸信會、長老會、衛理公會等大宗派,他們所拓展的教會無疑帶著西方宗派的色彩。
五十年代初期,所有的西方宣教士被迫離開,加上文化大革命時期有形的教會被摧毀殆盡,因此,有三十年的時期,中國教會可說脫離了西方宗派的影響。七十年代末期,在患難中僅存的家庭教會基本上已經走出自己的路,成為純然本色化的教會。
然而,改革開放後,西方的宣教士和海外的基督徒,以各種不同專職的角色進入中國,又漸漸把宗派的教義和作法帶進去。從八零年代中期之後,由韓國或東南亞到中國的宣教士,更以他們獨特的神學見解影響了大量農村教會。
中國農村的五大團隊:方城、唐河(中華福音團契)、安徽的穎上、利辛,以及溫州的團隊,可說都具備了宗派的要素。[9]今天的城市家庭教會,如北京的福音教會,是由門徒神學院所造就出來的傳道人帶領,他們承襲韓國長老會的傳統,實質上具有宗派的特色。
面對宗派興起的現象,我們一方面要肯定宗派的優點,一方面也要審慎評估其負面影響。有四件事,基督徒領袖必須看得清楚,且視為當竭力奮進的目標。
第一,任何人按著自己的背景、訓練與經歷,持守且擁護某一宗派的教義,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但不要以為自己的宗派可以涵蓋一切的真理。以下是陶恕(A. W. Tozer)博士的見解,他這篇文章的題目是:“自認正統的人要謙卑”。
“基督教很少是完美的。除了基督和祂所選召的使徒之外,世界歷史裡恐怕沒有一個信徒或信仰團體能純然持守真理。”
“有位偉大的聖徒認為,真理非常廣闊宏偉,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全然承受;需要透過整個蒙救贖的群體,才能完整反映出神所啟示的真理。”
范浩沙在《聖經的神學解釋辭典》中,也對此問題作了簡潔有力的說明:“沒有任何一個宗派、釋經系統、或解經方法,可以宣稱自己獨佔了對聖經——神的話——的詮釋。如果基督徒想要呈現耶穌的心思,就需要來自整個基督身體的見解,而這身體是由基督的靈所活化和引導的。”[11]
第二,必須學習和不同宗派的主內肢體來往,針對不同的看法有坦誠的對話,彼此尊重,互相欣賞。
2011年10月17日晚上,拜歐拉大學舉行了一場神學交流會議,邀請了在加州威敏神學院任教的何頓(Michael Horton),[12]和在貝勒大學教神學的奧爾森(Roger Olson)[13]進行非常具建設性的對話。何頓是加爾文主義的擁護者,而奧爾森則是亞敏念派的著名學者。他們兩位在公共的場合中交互辯論,並且分別出一本書,來為自己的主張作深入而中肯的分析。(註:何頓寫《贊成加爾文主義,For Calvinism》,而奧爾森寫《反對加爾文主義,Against Calvinism》)
當代有名的改革宗神學家弗雷姆(John Frame)認為,改革宗教會可以在其它方面向其他宗派學習,以便能更加進步。他主要是指實踐神學和建立教會方面,包括敬拜、傳福音、社會關懷、訓練牧職、和兒童主日學等。[14]
第三、在某些神學議題上,跨宗派或兼容並蓄的可能性。
已過世的福音派領袖司徒德(John Stott)曾經在《獨排眾議的基督》一書中提到,十九世紀時,加爾文主義與亞敏念主義的爭辯十分激烈,讓人困惑;而西門查理(Charles Simeon 1759-1836)的看法對他有很大的幫助。西門查理是劍橋畢業的卓越牧者和神學家,他曾經在聖三一教堂牧養長達54年,大半會眾都是社會菁英。他不懷疑聖經中有系統(因為真理本身不會前後不一致),但是他相信:無論是加爾文派或是亞敏念派,都沒有獨佔聖經的系統。[15]
西門查理曾這樣說:“真理不是在中間的,也不是在一端的,乃是在兩端的,……。有時我是在頂端的加爾文派,有時我又是在底端的亞敏念派;因此,如果這些極端合你的意,我就和你志同道合了。只不過要記得:我們所走的,不是一個極端,而是兩個極端。”
司徒德對這種神學的反合性提出解釋:“因為聖經的真理往往說得似非而是;而且,決心解答聖經一切矛盾的企圖,乃是自入歧途,因為那是不可能的。”有一次,西門查理笑著對他的朋友葛尼(J. J. Gurney)說:“你豈不知道鐘錶的齒輪,是向著相反的方向轉動麼?然而,它們都是為同一個結果效力。”
神學是建立在哲學預設上,並用人的理性去掌握聖經的真理。理性的思維總是在時空之內,然而神是無限的,祂超越時空。因此我們只能謙卑地承認,任何神學體系都無法把神性的完美與全備全然涵蓋住。
第四,在普世宣教和地區傳福音的事工上,以及慈善和公共議題上,教會應可密切合作,保持合一的見證,共同抗拒世俗化、人本主義、及無神論的潮流。
舉一個例子。“撒瑪利亞人基金會”(Samaritans Purse) 是由葛福臨(Franklin Graham)所領導的慈善機構,他們的同工在全世界從事公益的工作,藉此彰顯耶穌的愛。這事工是由許多不同宗派的信徒奉獻支持的,顯示教會在關懷弱勢群體和苦難的合一見證。
無論未來中國家庭教會的走向如何,宗派的形成與發展已有不可擋之勢。當然,中國的情形和西方截然不同,因為它有特殊的文化傳統和政經情勢。其實,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傳統家庭教會大部分還處於隱匿而封閉的狀態時,也有可以辨識的宗派特性,它是處境化必然的結果。中國教會開始自立、自養、自傳之後,一定會進入自己建構神學(self-theologizing)的階段。
筆者深盼,中國家庭教會能從西方基督教過去五百年來的歷史,學到寶貴的經驗與教訓,特別在宗派形成與建造中,我們不致重蹈“激進宗派主義”的覆轍。讓宗派的產生能對中國教會帶來祝福。
注
[1] Richey, Russell E., Denominationalism: Illustrated and Explained, pp. 2-3. 瑞契長期在宗派裡面過他教會的生活,很自然,他是從正面的角度來分析宗派的價值。而他以美國的宗派發展為主要的思考研究對象,沒有涉及第三世界在宗派發展過程中的特殊政治處境。
[2] Frame, John M. Evangelical Reunion: Denominations and the Body of Christ. p. 9-12. 弗雷姆目前是基督教界公認的最有影響力的改革宗神學家之一,他著作等身,曾在威敏神學院教授系統神學和護教學。2013年他出版Systematic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Belief, 使他變成當今的神學泰斗。
[3] McGrath, Alister, Christianity’s Dangerous Idea, p. 2. 麥葛福為今日出類拔萃的歷史神學家,在牛津大學任教數十年之久。此本書乃是探討基督新教如何從五百年前的改教運動發展至今,從歐洲到美洲、亞洲、非洲至全世界每個角落。在任何地區與文化中,基督信仰很自然發展出其特有的處境化模式,以便應對當時的挑戰。宗派運動在全世界應運而生,麥氏認為,「唯獨聖經」這一觀念乃具有高度的危險,必須妥善處理。
[4] Galli, Mark, “Sola Scriptura:Historian Mark Noll Helps Unravel the Uses and Misuses of the Bible Alone.”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017, pp. 50-53.
[5] Vanhoozer, Kevin J., Biblical Authority after Babel: Retrieving the Solas in the Spirit of Mere Protestant Chrstianity, pp. 112-117.
[6] Vanhoozer, pp. 143-146.
[7] Vanhoozer, pp. 188-190.
[8] Vanhoozer, pp. 189-190.
[9] 袁浩, “中國基督教與不服從的傳統:以王明道、唐河教會與守望教會為例”. 《基督教文化評論第四十四期:發展中的當代中國基督教和政教關係》,2016年,春。97頁。
[10] Tozer, A. W. Born After Midnight, pp. 76-79.
[11] Vanhoozer, Kevin J. ed., Dictionary for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p. 24.
[12] Michael Horton在維護改革宗傳統的神學護教上非常賣力。但他始終保持敞開的態度,來接受其他神學陣營的批評。2011年他出版The Christian Faith,奠定了他在當今神學界的地位。他與Roger Olson之間的對話,給神學的後進留下美好的榜樣。
[13] Roger Olson可謂是當今亞敏念派神學家當中最活躍的人物之一,他經常在Christianity Today撰文,表明他的立場。1999年他出版The 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twenty Centuries of Tradition & Reform,是透過亞敏念神學特有的眼光來解讀教會歷史的發展,被基督教界譽為神學佳作。
[14] 參王志勇, “改革宗可以向其他宗派學習,” 《恩福雜誌》2017年1月總62, 6-8頁.
[15] 司徒德, 《獨排眾議的基督》, 25-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