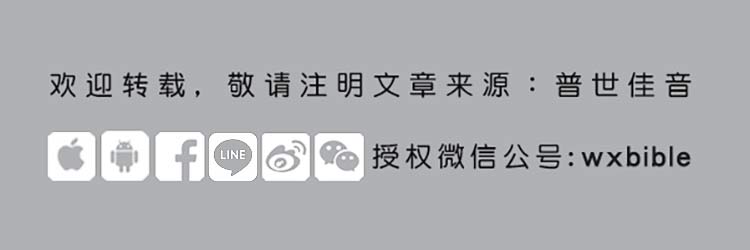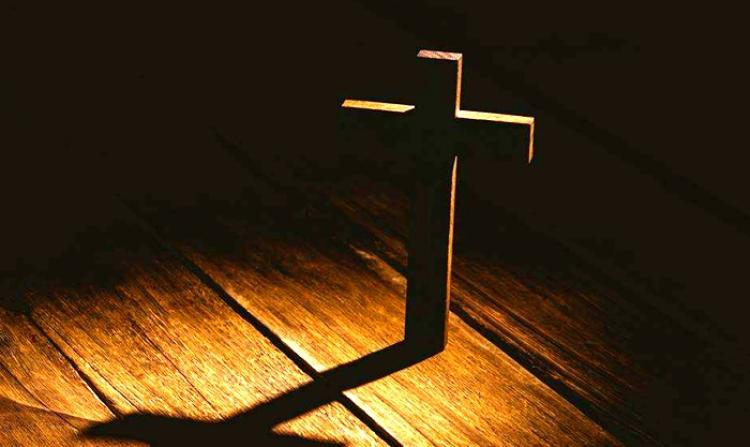“我有一個願望,這個願望一直主宰著我的生命;我有一個願望,這個願望始終鞭策著我的靈魂;一旦偏離這神聖的呼召,願生命的氣息離開我。不管世上有多少人反對,上帝的律法必定要堅立,為了民眾的福利,家庭、學校和國家都要遵行。全部聖經和整個世界見證,上帝的誡命要刻進國家的良知,萬國要奉行,萬膝要跪拜,萬口要承認——耶穌基督是主!”
——亞伯拉罕.凱波爾
二十九歲、單身的凱波爾當牧師之後,才從自己牧養的鄉村農夫身上對比,看出自己並沒有得救恩之道,從而真正悔改歸正。
看到現代社會碎片化的危機,他進入多個領域,身兼記者、報紙創始人、神學家、社會活動家、批判家、大學創始人、宗派創始人、政治家、黨派創始人和荷蘭首相(1901-1905)數職,他一生致力於用正統基督教信仰真理回應現代主義在各個領域中的各種公共思潮及謬誤。
他61歲(1901年)第一次應普林斯頓神學院教授B.B.華菲爾德(B.B.Warfield)的邀請訪問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的“磐石”講座一時轟動,直到今天仍影響到很多年輕人。普林斯頓大學給他授予法學榮譽博士學位。
他活到83歲,生前常需要四位秘書,在一張辦公桌前同時快速記錄下他踱步時對四個不同問題的論述筆錄。
他用荷蘭文寫的著作汗牛充棟,直到今天還正在被翻譯成英文(阿克頓研究中心的“凱波爾翻譯計劃”)。細讀他的人生和著述,你會驚訝於,在二十世紀還曾有人在公共社會中如此有力地實踐出基督教信仰。
在當代一些基督教思想家中,很多人例如薛華、范泰爾、普蘭丁格、沃特思托夫、提莫太凱樂、寇爾森等,都稱凱波爾是自己的思想導師。凱波爾傳統也孕育了北美很多高質量的基督教文理學院,如加爾文大學、多特大學、救贖主大學、聖約大學、凱波爾大學等。
教會史權威馬斯登教授曾說,凱波爾主義在北美福音派中的確傳播得很成功。富勒神學院前院長理查德茅也說,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凱波爾時刻”——在經歷基要派信仰從公共話語退卻的失敗之後,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基督教信仰需要一種公共視野和公共分析能力,來在思想界的公共生活中作光作鹽。
出人意料的“歸正”
凱波爾自己曾說過,“我們的思維方式不可避免地扎根於我們自己的生命軌跡中,就是我們在心靈和生活中所經歷的。”因此,認識一個人的思想,我們必須瞭解他的人生。
凱波爾的父親是一位荷蘭歸正牧師,不喜歡教會裡的激進派,一生致力於促進教會合一,也具有福音派人士的熱忱。凱波爾在教會中長大,但他後來回憶說,自己特別厭惡“那種基督教”,因為它已經變得空洞沒有活力,在各種道德問題上,配不上代表一種真理的信仰。同時,他也厭惡教會裡一種“虛假的保守主義”,對當代思潮只會一棒子打死,而不花時間去瞭解別人在說什麼。
凱波爾是一個擁有驚人的腦力的人。從他的肖像也可以看出這個特點(大腦袋)。幼年的凱波爾是他父親在家教育培養出來的。他直到中學階段才在雷登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後進入雷登大學,專攻文學、哲學和神學。他回顧這段教育經歷時說,自己在很多當代聖經批判的思想中,並沒有能力體察它們的謬誤在哪裡。這讓他心中一直有個空洞:“我的信心無法深入扎根在我那顆未歸信、自我為中心的靈魂中,在懷疑精神的炙烤下,必定會枯萎掉。”他在博士論文中將加爾文與一位自由派神學家Jan Laski相比較,表明自己比較喜愛後者。所有人都不能逃避自己時代的限制,凱波爾受教育的這段時間,正是歷史批判在歐洲學府佔據高地的時期,他的導師是自由派神學在荷蘭的倡導者。他自己也將這段研讀神學的時期,稱為自己人生“未歸信”的階段。
二十五歲時,他接受一間教會的呼召,在荷蘭一個名叫Beesd的小鎮擔任牧師。一開始,凱波爾認為自己的會眾(大多是農夫農婦)都屬於一種僵硬的正統派。但當他開始認識這些人、進入他們的每日生活時,會眾對屬靈事物的深度興趣、對聖經的知識、對一種整全世界觀的把握和他們對上帝恩典之主權的百分百肯定,深深觸動了凱波爾。他此前並沒有接觸過這樣一群人。他一開始覺得很遺憾,這樣一群人好像還是被鎖在宗教改革時期,他們無力回應現代社會的問題。
這段牧會經歷讓凱波爾回頭鑽研加爾文,在重讀這位改叫者對自己時代的回應時,凱波爾開始獲得一種新的使命感:如果說現代社會出現了一些反對基督教信仰的系統思潮,那麼教會就有責任作出系統性的回應。如果像加爾文所說,教會是信徒之母,那麼教會就又責任系統地牧養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信徒,在自己發揮恩賜的領域回應,而不只是退避到敬虔的一個角落,或試圖回到過去某個敬虔的時代。
這個農村小教會的確成為凱波爾的靈性之母,可能也是這個起點讓他後來成為教會的神學家(a theologian of the church),而不是學院派的神學家。
愛妻的影響
不過,誰也沒有想到,與此同時,把凱波爾拉回正統信仰的人,是他那位剛做過信仰告白、沒有什麼學識的年輕未婚妻。凱波爾在回憶錄中寫到,是妻子送給他讀的一本英國小說《瑞德克裡夫的繼承人》,讓他的心靈開始回家了。
故事中兩位主角的經歷、在葬禮前的悔改,讓凱波爾彷彿身臨其境。男女主人公在戀愛中因控制欲帶來的痛苦掙扎,也讓年輕的凱波爾正視自己在親密關係中的罪。最後他說,“當主人公菲利普跪下的時候,我發現自己也正合手跪在我的椅子面前。噢,那一刻我靈魂裡經歷的事,是我後來才完全明白的。但是,從那時起,我鄙視我此前愛慕的,開始渴求我此前所鄙視的。”他靈魂的錨,在那一晚拋在了一個穩固的磐石上。
凱波爾對妻子的愛慕和感激,也可以從他的這段歸信回憶中體現出來。上帝多麼美好的供應,讓這位“大腦袋”的神學家找到一位生命單純敬虔的鄉間女孩。他們結婚後一起養育了五個兒子和三個女兒。當你佩服一位神學家的思想時,可以去查一查他太太的故事,會讓你更加認識他本人。凱波爾的歸信故事,讓人想到另外兩個“大腦袋”思想家:C.S.路易斯和埃呂爾(Jacques Ellul)。
護教學家、文學家路易斯回憶自己歸信的一幕說,“那一晚,全英國那個最不情願的人,在上帝面前跪下折服了。”和凱波爾一樣,路易斯後來的信仰進深,甚至他最出色的幾部作品,都受到自己早逝妻子Joy的影響。
法國社會學家和神學家埃呂爾一生也著作很多,直到今日,還正在被人從法文翻譯成英文。他一生極少談自己的靈性經歷,只有在晚年太太去世之後,他接受過自己學生的一次個人訪談。當學生發表訪談之前,給他看稿子,他不太滿意於學生只在說他的成就,沒有提他的太太。他的學生只當這是一位喪偶獨居老人的可憐埋怨罷了。但埃呂爾繼續對他說,自己本是個喜歡在象牙塔作學問的書獃子,因為太太的熱情好客,才不得不把自己倡導的“小組教會論”實踐出來,常常帶年輕人去山裡露營,圍坐一圈開始談論人生、神學和哲學,實踐他在理論上論述的真正的基督教團契生活。
這三個夫唱婦隨的人間佳話,豈不令人羨慕。即便是作為思想家,人的靈性和愛情都是極真實的,夫妻二人在靈性和志趣上的融合也是自然發生了。
批判自由派的內行
作為一個前自由派,凱波爾對現代主義思潮帶出一種同情的理解,但這並沒有阻礙他更加犀利地批判它。他指出,自由派神學是被一種對現實的膚淺認識蒙蔽,而失去了對上帝、禱告、罪和教會等更加現實之事物的認定。此言與二十一世紀另一位思想巨人沃格林關於現代性之“次級實在”的批判觀點一致。
在凱波爾看來,深受泛神論和演化論影響的現代性問題是一個複雜的現象,是必然會產生的。他在批判時公允地與尼采等思想家對話,犀利地揭示出現代理論中的虛無和倫理謬誤。他的文化批判致力於揭示出當代各種精神現象的本質。
儘管凱波爾持有一種“高聖經觀”(high view of the Bible),但他反對製造一種“聖經崇拜(Bibliolatry)”。他將啟示與默示進行了區分(成文的聖經是上帝的“默示”,而“啟示”包括上帝持續向人揭示自己)。他反對一些聖經批判,但卻不是一個字意派的基要主義者,因為釋經要考慮到聖經作者使用的文體等因素。
凱波爾的作品將正統教義、對社會的分析和敬虔的激情結合在一起,以至於《凱波爾傳統全景》一書的作者在開篇就引用現代凱波爾神學權威John Bolt的話說:“你不能平平淡淡地介紹凱波爾,他的思想決不允許你這樣做!”為辯明真理、建造教會的熱心,從凱波爾的文字中湧流出來。
靈性是神學研究的根基
凱波爾的一生可以見證耶穌在馬太福音7章24-25節所說的:“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凱波爾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三隻小狐狸》,提醒基督徒要警惕智性主義和行動主義的危險,儘管他自己一生致力於這兩項工作。他呼籲教會回歸謙卑的靈性操練和誠實的學術討論。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在凱波爾和巴文克這樣的大神學家的大部頭著作中,很多篇幅仍是關於人在上帝面前之美好靈性的論述。
巴文克(1854-1921)比凱波爾年輕十七歲,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大學,1902年接替凱波爾的神學教授之職。凱波爾在1880年建立這所大學時,希望它可以成為在各個學科建立歸正思想的堡壘之地。人們常常把凱波爾和巴文克並列而談,因為他們在思想傳承上的確是近親。巴文克常強調說,傚法基督才是靈性生命的心臟。這兩位神學大家為靈性神學注入了有力的內容,也警告那些嘴上號稱“歸正”的人,在實際生命中顯出誠實、謙卑和恩典來。
誠實無偽的見證,會在一個人過世之後,仍長期發出馨香來。凱波爾只想做一個路標,指向基督。
作者簡介
李晉,現為加爾文神學院博士研究生。馬麗,現為加爾文大學亨利研究中心研究員。
李晉、馬麗夫妻二人同為社科和神學類譯者,譯有《自然正義》、《托克維爾的政治經濟學》、《致年輕加爾文主義者的信》、《寬容的不寬容》、《思想的境界》、《慷慨的正義》等書。
感謝著者授權“今日佳音”首發;版權歸作者及“今日佳音”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和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