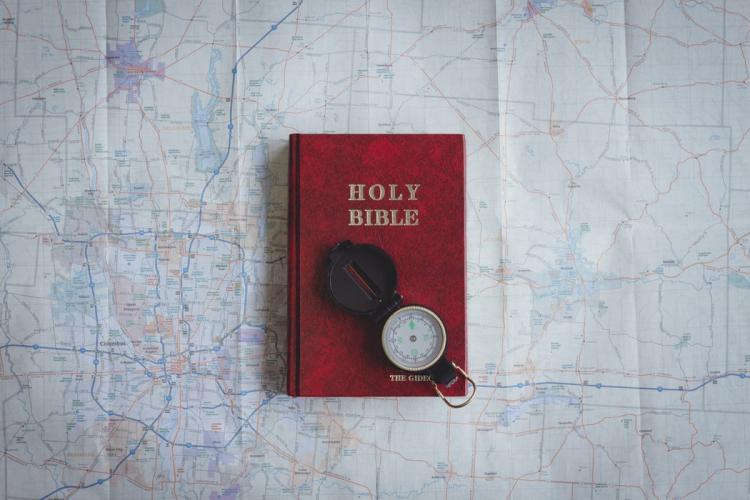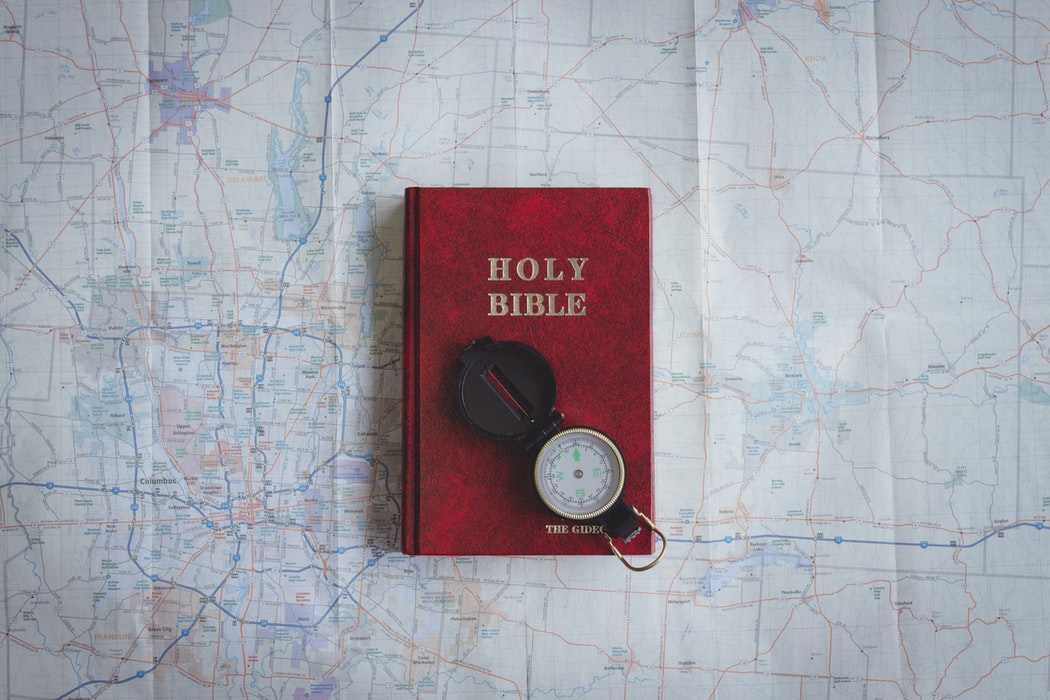
作者:王唯權
一場疫情,對教會的牧養和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促使教會不得不及時調整策略。而“沒有異象,民就放肆”(《箴言》29:18),一間教會的“神學異象”,往往決定了其是否能在變化無常的文化處境中,透過永恆不變的真理,提供反思以及實際回應的策略和方法。
本文是作者在12屆網路宣教論壇上的分享,以饗讀者。也歡迎您留言表達觀點。
地獄天堂皆真實,時刻準備歸天家
▼
01
何謂“神學異象”?
關於“神學異象”,提摩太‧凱勒牧師 (Pastor Timothy Keller) 在《21世紀教會成長學》(“Center Church”)中提到這個概念,這是他從戈登康維爾神學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神學教授林茨 (Richard Lints) 那裡借來的概念。凱勒牧師表示,“神學異象就是一個願景,你要在某個特定的時空裡,拿你的神學教義‘做什麼’⋯⋯它是針對某程文化、針對某個歷史時刻,對福音提出一份忠實的陳述,為生活、事奉、以及宣教使命,賦予豐富的意涵。”
簡而言之,這個概念涉及兩個基本範疇:神學教義的範疇,和文化處境的範疇。一個是有規範性的、永恆的、不變的;另外一個則是有描述性的、短暫的、是會改變的。
這個概念說明了每位牧者,在每一間教會,並且在每一個時空背景之下都應具備傳遞異象的使命。“異象”也可以理解為“目標”。當然我們稱它為“異象”,就是希望當牧者在傳遞這些目標的時候,是來自於上帝的感動,而非個人想法或主觀意識,或者是他的野心。
因為個人領受、事工目標往往是主觀的,但教會異象需要一個更客觀的基準、更客觀的運作框架,使它在被制定的時候能夠變得更實際和周全,而合乎聖經的神學理念就是這樣的客觀的標準。

02
面對疫情的神學反思
每一間教會的事工理念和異象,其實都來自於該教會以及它的牧者的神學理念和信仰告白。因為牧者要麼按著自己所宣認的信仰來帶領教會(有的人稱之為 Confessed Theology,或者是Confessed Beliefs),要麼就是按照自己的感覺、想法和理想來領導。
我們需要留意,世界上不被神學引導的事工理念,當中最主要的差異在於這些理念是來自於聖經,還是來自於聖經以外的根源(其中可能包括世俗文化、牧者主觀的想法、會友的訴求等等)?
所以當我們在面對新冠疫情,以及後疫情時代的一些牧養課題時,我認為我們都需要回到自身宗派的信仰傳統來做反思、回應,甚至進行“反擊式的行動”。要麼順服我們宣認的信仰,要麼就是順服我們主觀的偏見還有認知。
順帶一提,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夠把別的教會的事工策略和事工目標,直接搬到自己教會來落實的主要原因。因為每一間教會都有它認信的教義、既有的文化、預設的立場。其實教義、文化和立場也就是這間教會的“心”。只有在事工的策略、方法,跟這個教會的“心”是一致的時候,這間教會才能夠發揮它所當發揮的果效。所以這就是“神學異象”的價值。
“神學異象”能夠為教會在變化無常的文化處境中,透過永恆不變的真理,提供反思以及實際回應的策略和方法。

03
我所在教會在疫情中的“神學異象”
1) 牧者的身份:公共神學家
首先要和大家分享,我怎麼看待自己的身份。對我自己來說,我認為在面對這類公共課題的時候,我是一位公共的神學家。不過在這裡要補充,我對公共神學的界定方式跟一般的界定方式不一樣。我是跟隨范浩沙 (Kevin Vanhoozer)——三一神學院的神學教授來做界定的。對他來說,“公共神學”就是教會作為一個福音的群體所做的公共的見證,在公共領域見證福音的大能和工作。
范浩沙表示,牧者作為公共神學家的首要任務,就是幫助上帝的子民“成為上帝呼召他們該有的樣式”。正如《聖經·以弗所書》4:13所說,“直等到我們眾人在信仰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完全長成的身量”。而只有在教會成了它應當有的樣式之後,這個福音的群體才能夠在公共領域中作上帝榮耀的見證。
2) 牧者的職務:靈魂的餵養
那如果我的身份是一個公共神學家,我的任務是什麼?我的職務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靈魂的餵養。
我的首要任務,就是用上帝的話語來滋養信徒的靈魂並且堅固他們的信心。大家都非常熟悉《使徒行傳》6:4說到牧師的職責就是祈禱、傳道——透過祈禱實踐祭司的職份和責任,來陪同及帶領弟兄姐妹禱告,並且透過傳道來實踐先知的職份,向上帝的百姓來傳講上帝的心意。
所以,猶如剛才說明的牧師的職責,或對我來說作為一個公共神學家的職責是什麼?就是靈魂的餵養和引導。因為當一個福音的群體、信仰的群體得著建造,並且明白福音、理解福音、信靠福音的時候,他就能夠在公共領域中發揮這個群體應當發揮的功用。
在歷史中有許多關於牧者們專注於靈命餵養的記載:譬如在十八世紀,知名聖詩《奇異恩典》的作者約翰‧牛頓 (John Newton),他雖然是一個廢奴的支持者,但他卻沒有透過政治行動來完成他的訴求,相反,他專心地以牧者的身份來餵養威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 的靈命,使威伯福斯能在不妥協自己的信仰、不妥協自己的良心的情況下,在英國的議會中倡議廢奴法案。
除了這幾個群體之外,還有誰應當留守在疫情爆發之處呢?就是神職人員。因為神職人員是具有屬靈職務的人,他們不該逃跑。為什麼?馬丁·路德說,“因為當人們面臨死亡的時候,他們最需要的是屬靈餵養,通過話語和聖禮來鞏固和安慰他們的良心,並在信心上戰勝死亡”。
我相信這些神職人員和屬靈典範的意思並非是要我們忽略社會公義,我們不是要抵制或反對基督徒注重社會公義、公共參與或文化工作,而是作為一個公共的神學家、作為一個牧師,我們的職份不應當本末倒置,不應當因為疫情的緣故亂了分寸。作為牧者,我們首要的職份就是餵養弟兄姐妹的靈魂。

04
我對“神學異象”的踐行
1)確立我服事教會的神學異象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80後的牧者,當新冠疫情爆發的時候,我首先想做的,就是慈惠工作。我想去大量收購口罩,然後幫助有需要的人。作為一個牧者,我也很想參與在這些社會公義的行動當中。
然而正因為我是個牧者,我需要退一步思考、禱告,重新定義我在疫情中應當扮演的角色。所以就在禱告之後,我發現教會在疫情爆發的時候,其實並未預備好做這一類的工作。因為我所牧養的教會在今年3月底才剛建立兩年,我們有很多剛信主的慕道友,所以我自己的判斷和感覺是,我們需要的是靈魂的安慰、真道的裝備、敬虔的操練,並且為疫情過後來預備,為我們的事奉來整裝待發(當然當時我沒有想到疫情會維持這麼長時間)。
那麼,我們教會在這段時間具體做了哪些事呢?首先猶如剛才所說,每一個牧者都需要回歸、回溯他的神學傳統和根基,來思考他在這段時間要制定的“神學異象”是什麼。就在我反覆思忖之後,我認為教會作為一個信仰的群體,我們首先應當做信仰群體該做的事情,所以我就透過《希伯來書》10:19-25為大家制定在疫情當中的“神學異象”。
透過這篇信息,我向弟兄姐妹說明,疫情中,教會的任務、職務並沒有改變,教會的本質也沒有改變,我們仍然是一個信仰的群體。因此我們有三個要務:
● 第一,要用充足的信心來親近上帝;
● 第二,我們要在基督裡堅守所宣認的指望;
● 第三,彼此相顧。
而這樣的“神學異象”,也奠定了教會這段時間的講台信息和事工的安排。
2)講台信息之外對神學異象的踐行
在牧養方面,我們也安排了許多事工來提升我自己作為一個牧者的能見度。就像馬丁‧路德囑咐神職人員在瘟疫期間不可逃跑,要留守崗位。越是在疫情中、越是在動盪不安的處境中,牧師更需要在場,讓弟兄姐妹知道,他是隨時預備好來服事他們,甚至為弟兄姐妹捨命。
所以我們就在這段期間制定很多我們教會其實本來沒有做過的服事,譬如說“晨更”。我們從疫情一爆發之後就開始了每天早上晨更,一開始我們閱讀《加爾文的靈修與祈禱》,讀完之後我們就用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來做晨更。我們教會其實只有100多人,但是每天早上願意抽出時間,來到ZOOM平台跟我們一起晨更的弟兄姐妹有16-20人左右,我自己已經是相當滿足了。
除此之外,我們每雙週二有所謂的喝“查”聊天,這個“查”其實是來自於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Charlie(“查理”),所以就是喝“查”聊天。基本上就是我對全教會開放的時間,歡迎弟兄姐妹上網跟我聊聊天、一起禱告,沒有特定的議程。不過蠻有趣的,弟兄姐妹都非常渴慕,基本上每次喝“查”都不是在聊天,而是在查經,所以我為此非常感謝主。
週三我們繼續有禱告會,週四下午有伯克富的《系統神學》,晚上有《加拉太書》的查經班,週六早上有海德堡的要理問答……所以看得出來,我是非常盡力在做牧養、餵養、堅固信心、建造靈性、建造敬虔生命這樣的工作。
除此之外,教會當中也有年輕人在這期間願意發揮愛心,自發性成立了“送愛到鄰舍”事工,目的是希望為教會的長者以及行動不方便的弟兄姐妹採購生活日用品。
因為我們這麼做,弟兄姐妹的關係更好了,聚會的人數也不斷增加,晨更和禱告會的人數也有顯著增加。海德堡要理問答,一個神學性很強的課程,現在平均有三十多人是會固定來上課。所以透過這些事工和網絡崇拜,我們其實也在網絡上、小區中不斷地增加我們的能見度,吸引了不少在這段時間或者過去停止了聚會,或者正在尋找教會的弟兄姐妹。
3)遇到的問題和挑戰
疫情顯然為一些教會(至少為我的教會)帶來不少祝福,但其實也帶來了挑戰。我們實體聚會的時候,一直以來都有很多福音朋友,但因為疫情爆發,我們發現福音朋友,尤其是北美的福音朋友會比較被動,所以他們不會很主動地想要跟教會聯結,或者是要加入到教會的群組裡。因此我們的確流失了不少慕道的朋友,當然同時也吸引了很多有信仰或過去有信仰的弟兄姐妹,其中一個原因是跟我們整個策略相關。
不能實體聚會,為宣教的工作、福音的工作帶來不少的挑戰,這也是我們教會在這段時間不斷探索和思考的。如果上帝允許,我也希望在這段時間重新制定我們教會的“神學異象”,開始由內向外去做更多作光作鹽的工作、福音外展的工作、社會公義和慈惠的工作。
除此之外,在疫情中,教會吸引了不少離教會方圓30英哩之外的信徒,甚至外州的信徒。我的教會是在加州,這段時間也開始有一些紐約的弟兄姐妹加入我們,跟我們一起聚會,但是這是一個非常有挑戰的事情,因為我們需要思考教會是否能夠有效地去牧養這些遠程的弟兄姐妹。
當教會透過網絡平台吸引到不同教會的弟兄姐妹的時候,我們需要思考這其中是否涉及教牧倫理的問題,牧者應當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怎麼跟弟兄姐妹溝通、去傳遞正確的教會觀念?我們又是否要為了別的教會的良心多走一里路,主動去跟對方的教會進行溝通?進行怎樣的溝通、互動、同工,都是我們需要思考的。

05
未來需用“神學異象”來響應的挑戰
這次的疫情對教會來說,會徹底改變教會的前景,影響教會未來牧養的策略和資源的分配。雖然多數的牧者、學者都認為網絡聚會不可能也不應該取代實體聚會,但事實上已經改變了我們聚會還有教會的樣貌。如果一間教會過去在線下聚會是五、六人,改成在線聚會是十八、二十人的話,根據這種狀況,教會沒有道理要堅持過去的牧養模式,所以是一定會有改變的。
這段時間改成在線聚會之後,大家也都發現影音同工的重要性,但是我們需要問:教會是否重視這些事工?我們應當用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新媒體、自媒體,甚至實時通訊軟件的安全性等問題?
當然在面對這些議題的時候,教會不可能不去思考自己跟文化之間的關係,所以在面對文化議題的時候,我們需要思考,我們的態度是抗衡還是接受?改進還是合作?針對這些方面,我強烈建議有興趣的弟兄姐妹可以參考提摩太·牧師凱勒(Timothy Keller)所撰寫的《21世紀教會成長學》(“Center Church”),我想大家在當中會得到很多啟發。
除此之外,大家也可以參考柯羅奇 (Andy Crouch) 所撰寫的《創造文化》(“Culture Making”),他在其中說到面對文化的幾個態度:在科技和傳媒的使用上,我們教會的態度是譴責、批判、模仿、消費?還是我們用比較正面的態度?當然這也是柯羅奇所建議的一個看待文化的態度,就是培育,還有創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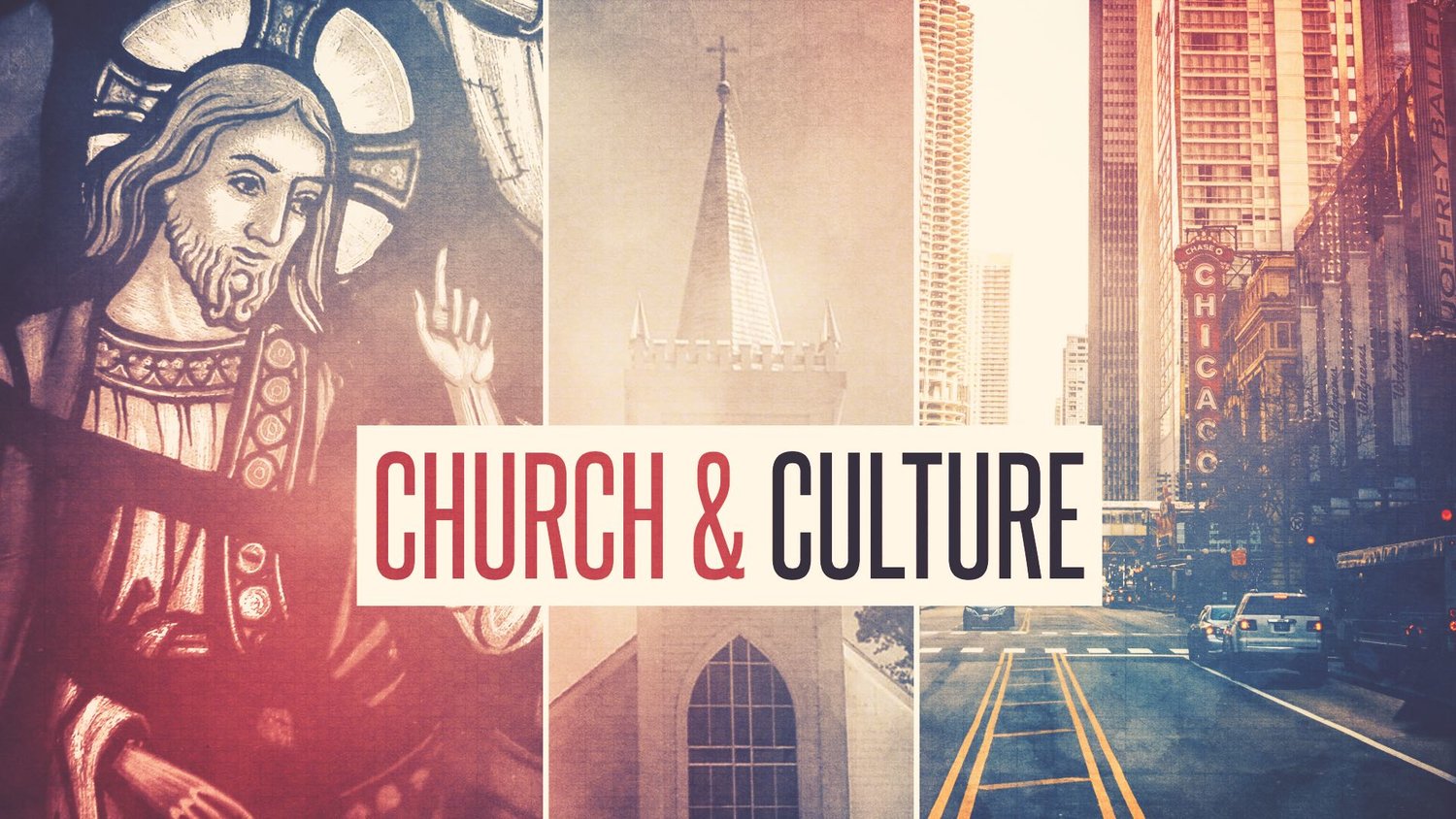
結語
未來還有許多我們需要面對的課題,甚至現在就有許多問題是我們需要面對的,而這些課題都需要我們透過自身教會的“神學異象”,以及我們的神學傳統來回應。
一方面,不論我們隸屬於哪一個宗派,或者是沒有宗派的,我們都需要不斷地在真理、教義、神學的理解上下功夫,使我們能夠“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非常睿智地去觀察、評估我們的處境,謙卑聆聽各個領域專家透過上帝普遍啟示所積累的洞見,憑著對上帝及其福音的信心,我們盡其所能地把所搜集到的數據整合、整理起來,來釐定一個合理合法的“神學異象”,以致於我們能夠藉此榮耀神、建造教會,並且祝福世人。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
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
- 箴言 29:18 -
- End -
譯者簡介:
王唯權牧師,來自台灣,現居美國加州奇諾(Chino),與妻育有一兒一女。本為音樂人,本科主修吉他演奏及聖經研究,於Talbot Theological Seminary獲得道學碩士,並曾於其擔任釋經學、歷史神學和系統神學的助教及研究助理。現任CRC(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基督教改革宗)焦點基督教會(CrossPoint Church)中文堂的牧師。
版權聲明:
本文完整版首發於《舉目》
轉載需聯繫授權
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