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蔓延,有一种宽容,是对邪恶的纵容!
渥太华大学宗教系荣休教授阿默曾写过一句常被人引用的话:“我们的观念中有一个认识,那就是,要做一位有美德的公民,就是要能宽容所有事物,除了‘不宽容’之外。”
全美拉姆凯阿尔法弟兄会的执行主席托马斯·海姆波克写过,“对新的宽容的定义是,每一个人的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对真理宣称的认识,都是一律平等的……并不存在真理的等级之分。你的信仰和我的信仰都是同等的,而且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尽管如此,如果这种新宽容观将所有价值观、信仰都高举为值得尊敬的地位时,人们就可以追问一个合理的问题,即,这种价值上的平等,是否也包括了纳粹主义和儿童献祭呢?或者,在这一点上,人是否可以把三K党和其他各样超级种族歧视团体的立场也当做是值得尊敬的立场呢?
在这种新宽容观之下,是不允许有任何绝对主义的;然而,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对绝对主义的绝对禁止。宽容掌管一切,唯一的例外是,不能有人对这种特殊的宽容定义持不宽容态度。
正如盖得所说的:“人们很难在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而他们却在另外一点上完全一拍即合:即认为不宽容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任何人该被别人冒犯。”
盖得的精妙洞见中,他提出三点澄清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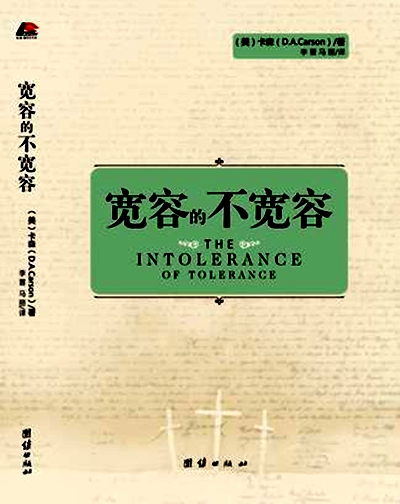
第一,旧的宽容观和新的宽容观都有明显的局限性。例如,旧宽容观会欣然允许伊斯兰教信徒在一个极少信奉伊斯兰的西方国家传教。它还可能发展到一个地步,允许激进的伊斯兰来别国传教,虽然它本身厌恶这样的信仰信息。但是,旧宽容显然不会允许激进的穆斯林信徒来轰炸人民和建筑:传教过程中会有互相冲突的反应,但暴力是不能被容忍的。在适当的时候,那些倡导这些暴力行动的人,可能后来会失去言论自由。同样的,新宽容观可能对所有宗教都很宽容,但却为那种认为自己有某种排他性救赎道路的宗教而担忧,理所当然也会反对那些主张用爆炸袭击其反对派的宗教。
旧宽容观和新宽容观都会以一个人作为例子:在一个拥挤的剧场里,这个人假喊了一声“着火了!”这个例子说明,在什么情况下,言论自由是需要设限的;在什么情况下,是不能一概讲宽容的。但是,大体上说来,两种对宽容的理解都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不管对宽容的理解是怎样的不同,他们常常也不在同样的场合对宽容设限。
更重要的是,如上所言,如果盖得的洞见是正确的话,旧宽容观是在对真理、良善、伤害和保护社会及其受害者的实质性论证基础上设定界限;而新宽容观则是在它认定何为不宽容的基础上设限的——后者已经成为最大的一种恶。新宽容观的倡导者们最乐于给他们不认同的人,贴上“不宽容”的标签,或一些类似的绰号:如,“偏执的”、“头脑狭隘的”、“无知的”等等。旧宽容观的倡导者们极少用不宽容的态度指责对手,相反的,他们的措辞是由他们对不可宽容的恶之认识塑造的(所以他们说安乐死的倡导者是在杀人,自杀式炸弹者是恐怖主义,等等)。
持有新宽容观的人最倾向于给对手贴上不宽容的标签,这一事实给我第二点反思。在西方文化中,“不宽容”的指责已经被赋予了极大的力量。它起到一种“胜出信仰”的功能。所谓“胜出信仰”,指的是一种打败其他信仰的信仰。例如,如果你认为一种信仰是正确的,你是不可能也认为其他信仰也是正确的:这种胜出信仰打倒了其他信仰,所以胜过了它们。例如,如果你相信,救赎之路不止一条,那些认为只有唯一的救赎的人,就会被看作是愚昧、不宽容的;那么坚持认为伊斯兰是唯一的救法,或耶稣是唯一道路的声音,对你来说,都是不可信的:你会觉得他们的信仰无知又不宽容,那个信仰一下子就被你自己的信仰打败了;你的信仰就是——可能存在多种通往救赎的路。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清楚地解释了耶稣是谁、他做过什么事,包括他的十字架和复活成了唯一人类可以与上帝和好的路径,我在上面描述的那个有胜出信仰的人,他可能会在智力上有兴趣听这个基督徒的话,但他会立刻不假思索地排除基督徒所说的一切。如果把几种胜出信仰放在一起,将它们广为传播开来,你就造出了一个“不可能结构”:与你的信仰相反的信仰,被认为是如此不可能,以至于不值得听,更谈不上觉得它有启发或有说服力了。
把最后两点反思放在一起,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之疆界,就变得十分令人怯步、担忧了。新宽容观倾向于避开对复杂道德问题的严肃思考,而把每件事都放在“宽容或不宽容”的坐标轴上进行分析,把所有不符合这个宽容尺度的,都从美德人士的先贤祠中赶除出去了。可能在这个立场中,最令人悲哀的是:它不能认识到,这种胜出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受文化塑造的。例如在中东,几乎没有谁敢坚定地说,他认为所有信仰都同样具有价值。在那里,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说只有一种救赎之路。当然,至于这条路具体是什么,人们仍然会争论。倡导新宽容观的人,更倾向于俯视中东的各种文化,他们会认为,如果这个地区的人都可以像持守新宽容观的人一样“宽容”的话,和平就会在那里得胜了。与此同时,中东的很多公民这样看待新宽容观:失去活力的人才相信这种立场,这样的人只把物质财富看为宝贵,并不思考什么是善恶、真理和谬误,更不用说关于上帝的事了。辩论的两方阵营中,都极少有人思考如何去建立一种文化,让人们可以在基要问题上激烈地否定彼此,而仍又可以宽容对方,因为他们都是以上帝的形象而造的。
第三,旧宽容观和新宽容观诚然都为“宽容”设定了界限,不过,我的意思从来不是说,旧的宽容总是正确,而新的宽容总是错误的。我的年龄让我还可以记起,在这个国家,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非裔美国人不能坐在公共汽车的前排:坐前排是不能被容忍的。如果说,我们今天如此在意政治正确性,以至于我们的担心已经超越了理智,另一方面,人们看到一些简化俚语(如中国佬、西班牙佬、意大利佬、亚洲佬)出现的时候,还是松了一口气。当然,歧视是永远不会完全消失的,而我们要持续不断地警惕、抵制之,才是智慧。
尽管如此,现代人对这种刻板歧视印象的警告,被传达出来的时候,会带着极大的贬低之意,在很多领域都是如此,以至于新形态的歧视像蒲公英一样在野地里蔓延开来。这就是詹姆斯·卡尔布巧妙称之为“严厉询问的宽容”。伯纳德·高德伯格将这个问题直白地表述出来:
问题是这样的,至少在我看来:多年来,我们越来越宽容所有正确的事,如公民权利。但是我们变得头脑越来越狭隘,多多少少变得不分青红皂白了。“你这么爱下判断啊!”这几乎成了美剧中一句最贬损人的总括之语,就好像对文化中的糟粕进行批评,是一件不好的事一样。
节选自《宽容的不宽容》,作者:卡森 译者: 李晋马丽。略有删节
如需转载请注明:
文章来源:普世佳音,支持各大应用平台APP下载
新浪微博:普世佳音
授权微信号:耶稣基督圣经福音,wxbible


编辑流程:
发布时间:
繁體版:
Line?:
栏目:
机构: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