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幻想征服自然,却遗忘了自己管家的责任
“人征服自然”(Man’s conquest of Nature),人们常用此表述应用科学之进步。“人击败自然”,有人很早以前给我的一个朋友说。这话之语境,有种悲剧之美,因为说者当时病危,是肺结核。“不打紧,”他说,“我知道我是因果律的一部分。无论胜利者一方还是失败者一方,当然都有因果律。但是这不能更改这一事实,还是胜利了。”
我选择这一故事作为起点,只是为了说明,我并不愿诋毁在所谓“人的征服”进程中所有真正利好,也不愿诋毁使之可能的所有献身和自我牺牲。交待过后,我必须前去对此概念作略微细致之分析。在什么意义上,人拥有了对自然的逐渐增长的权力?
让我们考虑三个典型事例:飞机,无线电和避孕药。
在和平年代,一个文明的共同体里的任何人,都可以花钱来用这些东西。但是严格说来,他这样做,并非在实施自己的或个人的控制自然的权力。假如我花钱让你背着我走,我本人并不因此而身强力壮。我所提及的这三种东西之任一或全部,一部分人都可以不让另一部分人使用——那些销售者,批准销售者,拥有生产原料的人,或制造商。
我们所谓的人的权力,究其实,是一部分人所拥有的权力,他们或允许或不允许其他人得其好处。再说,就飞机或无线电所展示的人的权力而言,人既是权力拥有者,又是承受者或其臣民,因为他是空袭和宣传的目标。就避孕药而言,在一种悖论的、否定的意义上,已降世为人者施加权力,未来一代则是其承受者或臣民。仅仅借助避孕,他们之存在就被否定;把避孕当作优生手段,未经他们同意,他们就被造为某代人出于自身考虑而选择的那个样子。从这一视点来看,我们所谓的人控制自然的权力,到头来却是一些人施加于另一些人的权力,自然只是其工具。
抱怨人滥用科学赋予他们的权力,抱怨人以之对付同类,这已是老生常谈。我要说的当然不是这一点。我不是在谈,那种提升德性就能治愈的败坏和滥用。我在想,所谓的人控制自然的权力,必然通常是且本质上是什么。
毫无疑问,原料或工厂公有制或科学研究由集体控制,能够改变这幅图景。然而,除非我们拥有一个世界国家,否则这仍然意味着一个国家凌驾于其他国家的权力。可是,即便在这样一个世界国家之内,或一个民族国家之内,这仍然(大体上)意味着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权力,以及政府对民众的权力。而长远意义上的权力施加,尤其是优生,必然意味着前一代人对后一代人的权力。
最后一点常常得不到充分强调,因为那些写社会事务的作者,还没有学着去效法物理学家,把时间纳入维度之中。为了充分理解人对自然的权力,从而理解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权力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勾画人类图景时,必须加入时间之维,起于其出现之时,迄于其消失之时。每一代人都向其后代施加权力:而且每一代人,因为他改造遗留下来的环境并反抗传统,都抵抗或限制其前代的权力。这就修正了这幅图景,即,不断从传统中获得解放以及对自然进程的不断控制,其结果就是人的权力的持久增进。
实际上,假如任何时代借助优生学和科学教育,获取随其所好左右其子孙后代的权力,那么,后生之人当然就是这一权力的承受者。他们更脆弱,而非更强壮:尽管我们把更为精妙的机器交他手上,但是我们已经预定了他们如何使用。再假如,而且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如此获得对其后代最大权力的时代,同时也是从传统中获得最大解放的时代,那么,它就会致力于削弱其前代的权力,剧烈程度与削弱后代权力不相上下。而且我们必须谨记,除此之外,后来一代来得越晚——生活时代越接近人类这一物种灭绝之日——极目向前,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少,因为其臣民将会变得越来越少。毫无疑问,只要人类还幸存,人类作为整体,其所拥有的权力会稳步增长。那最后的人,与其说是权力之继承者,不如说他将是所有人里,对伟大规划家和配制师之阴魂最服服帖帖,施加于未来的权力也最小。
鼎盛时代的真实图景是——让我们假定公元后100世纪——它最为成功地反抗此前所有时代,也最势不可当地主宰此后所有时代,因而是人类这一物种的真正主宰者。然而,在主宰者这一代(其本身是人类这一物种中极少的少数)之内,施加权力者将会是更少的少数。假如许多科学规划家美梦成真,“人征服自然”就意味着几百个人对亿万人之统治。在“人”这一方,那里没有也不会有权力的单纯增加。人所赢得的每一新的权力,同时也是凌驾于人上的权力。任何一个进步,既使他更强壮,也使他更脆弱。在每一次胜利中,他是凯旋将军,但同时也是尾随凯旋车队的囚徒。
本文节选自《人之废》,正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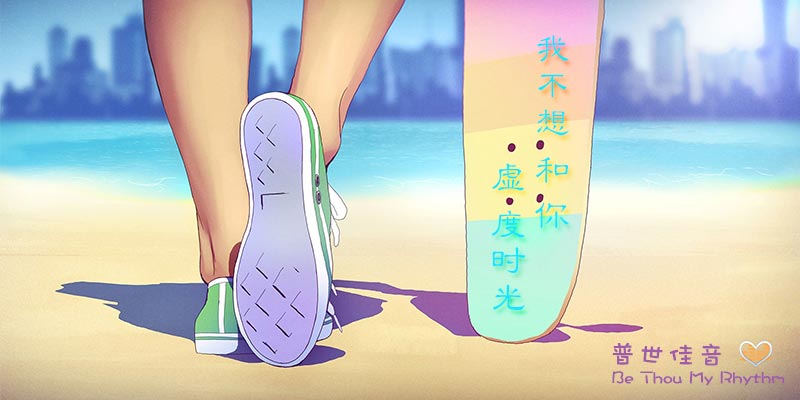

编辑流程:
发布时间:
繁體版:
Line?:
栏目:
机构:
作者:

